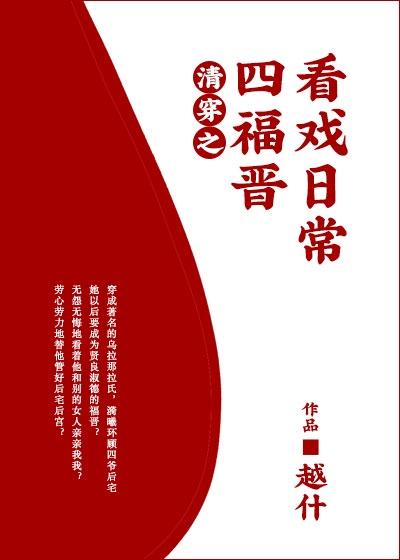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天真 > 第102章 涂初初x裴墨3(第3页)
第102章 涂初初x裴墨3(第3页)
“不耽误你睡觉。”
“会滑出去的……”
“不会的。”裴墨云淡风轻,吻她,“你又不是没这样过过夜。”
“……”
“裴墨。”涂初初心累,真诚地道,“你要是下次抓住我蹦迪。”
“嗯?”
“要不还是把我打死算了。”
“……”
裴墨失笑,低头亲她唇角。
涂初初实在太困了,昏昏沉沉闭上眼。
彻底坠入梦乡之前,听到他声音低低地,在她耳边说:“怎么会打你。”
他轻声:“喜欢你都来不及。”
太轻了,后半句话,像一个梦。
涂初初梦见爸爸。
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他很少入梦,偶尔几次,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拎着双皮奶或者别的小点心,站在放学时熙攘的人群里等她。
她小跑过去,他就伸手过来牵她,稳稳握牢她的手。
一边走,一边用那种熟悉又温和的语气,问她:“初初在学校有没有多喝水?最近降温,你住校也要多穿一点,不然很容易生病的,爸爸总不放心你。”
她听到后半句话,就开始掉眼泪,止不住一样,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周围环境都扭曲了,父亲起先手足无措地问她“怎么了初初,是不是有人欺负你”,没一会儿,他慢慢跟人群一起羽化、消失。
好像被人推了一把,将她推出梦境,她从中跌落,困难地睁开眼。
还是白色的天花板,吊顶,起起落落的窗帘……
视线无法聚焦,口干舌燥,有人附在耳边,低声叫她:“……初初,初初,你哪里不舒服,跟我说好不好?”
新的一天,清晨,阳光无声入户,清风卷起白色窗帘的一角。
静谧的房间内,裴墨亚麻色裤腿卷起,半跪在床头,帮涂初初测了体温,准备给她物理降温。
刚把她的小细胳膊从被子里薅出来,就看她很不舒服地皱眉,迷迷瞪瞪开始掉眼泪。
“初初。”她好像被魇住了,裴墨放下稀释的酒精,躬身抱住她,哄小孩似的,轻轻拍后背,“初初。”
涂初初迟缓地清醒过来,双眼无神趴在他怀里,茫然地盯着别处看了好半晌,才小声:“裴墨。”
裴墨稍稍放开她,叹息:“你是不是又梦到爸爸了。”
涂初初垂下眼不说话,浑身没力气,小章鱼似的趴着,蜷成一团。
“难受吗?”裴墨明明刚看过她的体温,将她抱在怀里时,还是忍不住伸手轻轻碰她的额头,“我早上醒过来,就发现你在发烧。你昨天半夜出门,也不多穿一点。”
涂初初愣愣地,腮边挂着好大一颗水珠,长而卷的睫毛上雾蒙蒙的。
听他这么说,她眼睛一眨,又一颗泪滚下来。
“难道不是怪你吗。”她可怜巴巴的,嗓音又软又哑,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说了不行……你非要折腾我,我就是被你搞发烧的。”
“……”裴墨失语,“不是,你是着了凉。”
“就是因为你。”涂初初不听不听,小声尖叫,“你太久了,你不是人。”
“行。”她平时天不怕地不怕,每次一生病就变得很脆弱。裴墨不跟她讲道理,抱着她轻轻拍,伸长手臂去够床头柜上的稀释酒精,低声,“是我不对,委屈我们初宝了。”
初宝……
涂初初眼眶发酸:“那你下次?”
“下次的事下次再说。”裴墨闷笑,手指有一点热度,酒精在她手背徐徐揉开,“还早,今天没课也不用回学校,你再睡会儿?”
“我生病了,你才让我睡觉。”她控诉他,“我昨晚说我想睡,你都不准我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