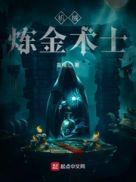墨澜小说>落日熔金 > 第8章(第1页)
第8章(第1页)
方识秋总是在昏睡,脑海中吊诡的幻觉已经随着梁暝的离去一同消失,迟钝的大脑也察觉到了异样。他的身体时常疼痛,虚弱得甚至连在房间里走动这样简单的事都无法做到,更别说追究那份古怪的根源。窗外的红日升起又落下,呼啸的风雪肆虐又消融,松树的枝条折断又新生,方识秋在温暖的牢笼里浑浑噩噩地消磨着不知何时会熄灭的生命。遗忘或许会更轻松一些。他这样告诉自己。哑女将清粥放在沙发旁的小桌上,没有马上转身离开。方识秋透过屋里昏暗的亮光看着她憔悴的侧脸,依稀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试图和她说话时发生的事情。那时他刚刚拆去固定在手腕和脚踝上的石膏,被梁暝抱到沙发上,那个将他从雪地里捞出来的女人端着炖煮好的食物走进房间。许久不曾见到除了梁暝以外的人,在女人摆好餐具后,方识秋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还未等到女人回答,一旁的梁暝突然暴怒而起,狠狠揪住了她的头发。托盘和水杯摔落在地上,瘦弱的女人重重地摔在地上,像即将送入屠宰场的将死的牲畜一般被拖拽下楼。梁暝愤怒的咆哮和从大敞开的房门传了进来,方识秋浑身颤抖着,抱着手臂蜷缩在沙发上。一阵木棍抽打肉体的闷响之后,他听见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和自己骨骼断裂时发出的声音如出一辙。那本该是很疼的,可女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不能说话,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哀求,只能沉默地忍耐一切。楼下殴打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钻进方识秋的耳朵里,面前的晚餐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粘稠的奶油包裹着炖得软烂的蔬菜,他看着只觉得一阵恶心。“秋秋不饿吗?”不知何时上来的梁暝站在门边轻笑着。他手里抓着哑女的围裙,慢条斯理地擦试着手上的血迹,从指尖到指根,连皮肤细小的纹路都没有漏过。那块染血的白布最后被扔进了燃烧的壁炉。火焰吞噬着木柴和布料,壁炉餍足地吐出一个冒着黑烟的饱嗝。黑烟在空荡的房间里散开,终于回过神的方识秋才惊慌失措地抓起了勺子。他舀起一大勺白色的黏糊物体,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奶油从无法完全闭合的唇缝里溢出,顺着嘴角向下淌,又在滴下前被擦去。“慢点。”梁暝半弯着腰,手里拿着沾了奶油的纸巾。方识秋强忍着恶心,用力地扬起头,将完完整整的没有嚼碎的土豆咽了下去。哑女消失了很久,一直到梁暝离开别墅,方识秋才再次见到了她。她的小腿打着绷带,走得很慢,动作不如之前利索,托盘里的水和食物总会洒出来一些。液体黏糊糊地挂在外壁上,哑女就用围裙小心翼翼擦去洒出来的液体,动作间不小心露出了手腕上的黑色手环。熟悉的黑色皮环刺痛了方识秋的眼睛,细微的触电般的痉挛从脖颈向四肢蔓延开来,在刚刚愈合的关节处隐隐作祟。“谢谢。”他低声对哑女说。“对不起。”哑女握着水杯的手晃了晃,洒出的水顺着水杯和手腕向下淌。她微微侧过了身,没有应答,只是低下头将那双混沌的眼睛藏在阴影之下。从那天起,方识秋没有再尝试和哑女说话。他不被允许离开房间,不被允许与梁暝以外的人交流。不论是单向的言语,还是双向的书写,又或者是眼神上的对视。他将哑女当作别墅里游荡的孤魂,竭力忽略她的存在。哑女的过去被埋葬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中,她的名字,她的身份,来到这座雪山别墅前所有的经历,方识秋一概不知。他唯一知道的,只有哑女并非先天失声这一件事。她不会手语,偶尔和梁暝交流时只会胡乱地比划着手势,却又精通急救知识,看得出曾经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方识秋烧得迷糊时曾幻想过哑女站在手术台前沉稳从容的样子。他猜,或许她曾是某所顶尖大学的医学生,又或是挽救过无数生命的医护人员,才会被梁暝关在这里。哑女应当是很聪明的,不会手语恐怕是因为致哑的过程粗暴惨烈,没能给她留足学习的时间。真可怜。方识秋同情地想。但他无暇顾及他人悲惨的命运。野雉慢慢走出窗户的边界,方识秋收回飘散的视线和思绪,后知后觉注意到了哑女的存在。本该离去的女人安静地站在一旁,如同一个毫无生气的死物,不知多久前送来的清粥还在冒着热气,放在一旁的陶瓷勺子下压着一张对折起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