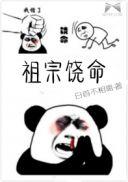墨澜小说>莫须有 荒唐言 > 第136章(第1页)
第136章(第1页)
哪知上次出门没看黄历,父皇身边还跟着这位姑姑和一众亲王,父皇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那个女人,开口却拒绝了她:“先帝从未将它给过别人”安乐顿觉被拂了面子,大感面上无光,都是那个女人!让她在众人面前白白丢了面子!成了个笑话!还有上上次!她曾自做诏书,蒙住前面的内容,请父皇画押,父皇笑着答应她,她那时竟还当了真,在百官面前上奏请立为皇太女。那个该死的左仆射魏元忠却劝谏父皇不可如此行事。她气的咬牙切齿:“魏元忠是山东愚顽倔强之人!父皇怎能与他商议国事?!武后且为帝,本宫是皇帝的女儿!有何不可呢?!”她那孱弱的父皇左右为难,只打算当个和事佬,便草草将此事揭过,不了了之这些仇她可是一个都没忘呢!现在倒好,这个女人又找上门来!当真以为她们母女俩好欺负不成?!“放开!”安乐怒道,眼见又挣不开双手,只好躲着脚,含泪朝韦后求救“母后!”韦后见情势不对,只好朝那人赔着笑脸道:“太平,何必与小孩一般见识呢?安乐她还小,不懂事”太平闻言轻笑一声,她玩这套的时候,韦后还不知道在哪里喝西北风呢。她一松手,放开了徒劳挣扎的人,扯着嘴角漫不经心:“安乐还小,你身为母亲竟不知阻止教导,反倒还来谴责本宫?”她背过身,摊开手耸耸肩,回头接着说道:“都是有孩子的人了,又能小到哪里去呢?”应邀前来的皇亲贵戚们顿时就不困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里满是揶揄,毕竟,懂得都懂,这位安乐公主,可是未婚先孕,闹出了丑闻,中宗迫于舆论压力,这才不得不下诏,将心爱的女儿嫁给武崇训这小子。韦后闻言先是面色一僵,又不好发作,只好接着和稀泥打着圆场:“这大喜的日子,还是莫要说这些个不吉利的话了”方才愣着的太监这才赶忙反应过来,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接着仪式上的流程,众人眼见没了瓜吃,只能扼腕叹息,继续百无聊赖地,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待到仪式结束,太子殿下连忙赶上抬腿便要上轿的人。“等等!”那人身旁的一位年轻人却拦住了他,不卑不亢朝他询问道:“太子殿下可有事?”“方才多谢姑姑!”他高声道,生怕那人听不见。金舆内的人无奈地扯了扯嘴角,若不是婉儿嘱托她,她哪有心思照看这位小辈?“知道了”谢奕听了公主这话,便已知公主实在没有闲情搭理这位太子殿下了,于是便再次拦住想要说话的太子殿下,委婉道:“前些个日子事务繁忙,公主确是有些乏了,还请太子见谅”他拱手告辞,便转身驾着金舆离去,徒留本还有些话要说的太子殿下在原地。“人家救你,不过举手之劳,自己这般,倒是显得有些自作多情”太子殿下懊恼地想着,一时之间,又怕被当作攀附权势,只好心神不定地领着一群人启程回了东宫。“母后!你看她!”安乐公主跪在韦后的双膝旁,哭诉道。“唉哟哟,母后的心肝啊”韦后一面好生安慰着自家闹腾的女儿,一面又道:“过些日子,母后自有法子教训她”“当真?”安乐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一向宠她的母后,毕竟就连父皇,对那个女人过分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韦后一笑,朝女儿保证道:“自是当真!母后什么时候骗过你!”安乐闻言喜笑颜开:“母后最好了!”不久,唐中宗任命女婿杨墩、武崇训为太子宾客。杨、武二人皆年轻轻浮,平日只是“蹴鞠猥戏”,以此取悦李重俊。“殿下理应明四书五经,仿贤人所为,怎么能整日与武崇训一行人等寻花问柳、只顾赌钱踢球呢?”李重俊身边的亲信宁业初见太子殿下昨夜宿醉,一早起来便浑浑噩噩的,一幅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模样,痛心疾首道。宿醉的头痛让他心烦的很,他不耐道:“武三思位高权重,又对本宫甚好,本宫与其子结交,不正是为了日后能多一份保障么?怎地你又说!”宁业初仍是忧心仲仲地劝着:“太子,二人皆口蜜腹剑也,岂能信”却被李重俊猛地打断:“行了!”“本宫自有打算!何须你多置喙?!”宁业初无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还太子殿下与武崇训等一行不作为公子哥去晃荡那些个勾栏瓦舍,赌场酒楼。眼见不得法,自己又什么都做不到,实难尽责,宁业初长叹一声,奏请自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