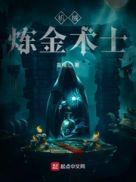墨澜小说>娇宦 > 第328章(第1页)
第328章(第1页)
清晨的养心殿,所有的人声和喧嚣依稀都在远方,与这里全无瓜葛,耳畔没了童稚的声音,她那颗心也更加空怅寂寥。明明刚才想去歇着,这时却好像忘到了脑後,人只是浑浑噩噩地信步往前走,也不知该去哪儿。这是干什麽,生死一线也不是没经历过,那时都能泰然处之,何以现下却如此不堪?何况前日在那片雨檐下不都已说得一清二楚的麽,不过就是他手上的一颗棋子而已,除此之外便两不相干。既然如此,为什麽还要这麽难过?嘴唇干得发疼,舔抿了下,淡淡的咸腥在口中晕开。血的味道半点也不好。萧曼脑中懵懵然,觉得该去倒杯水喝,停住脚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竟已走过了大半条通廊,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就是他惯常批红的隔间。每到夜间,她就端着精心熬制的粥水汤羹进去,再坐下来,一边替他分拣堆积如山的奏本,一边暗觑他将那一碗慢慢地吃下,玉白的脸上微起暖晕,自己心头竟也是热的。有时他会说些闲话,有时各自专注,默然相对几个时辰,直到天色泛白也不交一语,如此单调,疲倦至极,竟也不觉得厌。究竟有多少次,她记不清了。但却记得,他已经整整三日没有来养心殿,自己也再没有看到过他。可她却控制不住那双腿脚,还是继续往前走,脑中竟生出一个蠢笨之极的奢望——也许他已经在那里,或者说,哪怕能看一眼那书案上熟悉的陈设摆放,心下便能安适些。才刚迈出腿去,那隔间内便传来脚步声。萧曼浑身剧震,一霎间像能听到胸腔里怦然的跳动。然而那份激动才刚涌起便又沉了下去,因为庞杂的脚步显然并非只有一个人,其中也没有他。两名内侍很快从里面走出来,每人手上都是两大摞厚厚的奏本,一见她在门口,赶忙上前嗬腰行礼。“督主……来过麽?”她忍不住还是问了句,粗哑干涩的声音却连自己都吓了一跳。“回秦少监,二祖宗没来过,是司礼监刚传了话来,叫把前些天积下的本子一并都拿过去,奴婢们也不敢问,这半晌才收拾好。”还用问麽,这便是不会再来的意思。可是至於麽,他眼下是宫里真正的主子,底下数万人,生死都捏在手上,自然也包括她在内,何苦为了不想见费这个周章,难道还怕起什麽纠缠麽?她苦笑,也觉得好笑,那颗心却像凭空裂开,血涌出来,弥散在胸腔里,连同身上最後那点力气消散在四肢百骸。好累啊,记忆中从没这麽精疲力尽过。萧曼记不清自己是什麽表情,也不知道是怎麽转身离去的,她只想走开,找个别人瞧不见的地方呆着,脚下是虚浮的,只能一步步向前挪,喉咙不知被什麽东西堵着,那口气怎麽也上不来,沁沁的阴冷袭绕全身,整个人天旋地转。也许这宫里从来就没有过情,更不会因她而生情。所以,可笑的不是别人,只是她自己。终於支持不住了。她踉跄地向前倒,伸手好不容易攀住窗棂,才没倒下,烦恶涌动的喉间却再也压制不住,张嘴呕了出来,眼睑胀痛,泪下决堤。梦里琼枝脚下是空的,身子是浮的,连神识都在虚游飘荡,唯有耳畔是一片嘈乱的噪响。是风声麽?怎的似乎又能听到欢笑和鼓乐?的确怪得有点邪门,但说到怕,却怎麽也及不上眼前这片混沌的黑暗,杳冥如夜,不知身在何处。这情状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一丝细节来。过了多久呢?她也不知道,总之是度日如年,茫然忐忑间,脚下忽而有了着落,不再是悬空的,却颠簸摇晃得厉害。那片重重遮挡的黑幕霍然而散,耀目如刺的光冷不丁一下戳入眼中。她只觉目眩得厉害,晕了好一阵子才慢慢看清自己竟身处轿中,轿帷是锦绸彩缎的,而她身上则是凤冠霞帔,云襴大袍,一色的鲜亮喜庆,荣艳华贵。她猛地一惊,心下如明镜反照,忆起了些东西,但大半还是混沌不清。侧眸朝窗外望,丝帘也遂心之意似的恰在此时拂撩而起。没错,那外面是漫山遍野,夹道而立的黄栌树,层林浸染,满目绯红。美景当前,如诗如画,她却生不出半点赞叹赏心的意思,只觉那片围聚在周遭四野的红像熊熊烈火,更像血,光是瞧着似乎便能嗅到一股腥郁之气。她浑身悚然一震,蓦地里又记起了几分。几乎还没来得及反应,数道寒光就穿透进来,犹带温热的鲜血泼洒在华丽的轿帷上,又溅污了她的喜服霞帔,顷刻间便染透进去,那片红立时变得触目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