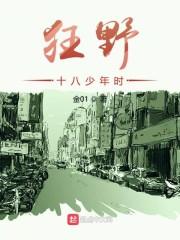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穿成汉武帝的家庭医生后 > 第 128 章(第2页)
第 128 章(第2页)
司马迁的家中有些地位,但牵涉不到朝廷机要。自然也得不到最准确的消息。他特地来找她,怕是真真假假的传言听多了,自己也难分辨。
“你是想问,李敢他是不是因为想刺杀大将军,反被骠骑将军杀死的?”
司马迁的神情空白了一刻,似是没料到江陵月会这么直白。而她的问题中,其实已包含了答案。
“没想到,果然……”
他咧了一下嘴,似乎想做出什么表情,但最终失败。末了,只肃容道:“多谢景华侯告知我实情。”
“这没什么。”江陵月道:“不过,你会把这件事写进你家正在编纂的史书中吗?”
“您怎会知道!?”
江陵月眨了眨眼,含糊道:“嗯……因为令翁乃是太史令啊,写些史书什么的不是很正常。”
不,真正的原因是,你后来真的写了《史记》啊。不仅如此,还把“鹿触”的借口给记录了进去。霍去病也因此和鹿有了不解之缘。
司马迁不疑有它:“是,家父正在整理些史料,打算编纂成书,供后人参考。”
说到这里,他年轻的面孔上流露出郑重和向往的神色:“家父也提前和在下约定好,若他有生之年不能穷尽,就交由在下来写完。”
原来这么早的时候,司马家两代人就有这个志向了?即使江陵月对他的偏颇颇有微词,此刻也说不出什么刻薄话来。唯有一声微不可查的喟叹。
“加油啊,期待我有生之年能读到。”
司马迁自然看得出来,眼前年轻明媚的小娘子对他的勉力做不得假。饶是他的心思沉静,此刻也难免生出被肯定的熨帖之感,言语中带出些真实想法。
“传言果然不能尽信。景华侯的平易近人,远不似其他跋扈之人……”
言语之间,不乏明珠蒙尘的叹惋之意。
江陵月:哈?
她联想到后代的一些传言,难免生出些许不详的预感来。南宋的黄震就锐评过:“凡读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司马迁的左卫右霍的态度则更加明显。
如果说,他对卫
()青的态度颇为微妙,对霍去病的态度就是显而易见的不喜欢了。他现在又这么感叹……
“你说的跋扈之人,不会就是,呃,霍去病吧?”
司马迁:“……”
他再一次被江陵月的直白噎住了。那来不及收回的错愕表情,也明晃晃地告诉江陵月:她说对了。
江陵月一阵无语凝噎。她早该想到的呀,刚才说到李敢死因之前,他就提了一句任安没出席丧礼。但他和任安的关系是历史上认证的好,自然不会怨怪他什么。
所以那一句话,矛头指向的其实是卫霍。
“好吧……”
她单知道司马迁对这两人有偏见。没想到,这偏见竟然来得这么早、又这么深。
司马迁尴尬极了。
对一个年纪尚轻的人,被对面看透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更何况,论年龄,景华侯还要比他小上数岁。他在心里编排的对象……刚好还是人家的对象。
这哪里是君子所为呢?
他逃避似地低下头去,不敢直视对面的目光,也咬着牙没为自己的想法辩解一句。他要是辩解了,那和当面说冠军侯的坏话有什么区别?
更加不是君子所为了。
司马迁丝毫不知道,江陵月正一瞬不瞬地看着他,以一种极其复杂的目光。
讨厌卫青和霍去病的人,司马迁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后世即使洒脱如苏轼,也用难听的话狠狠地编排了卫青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