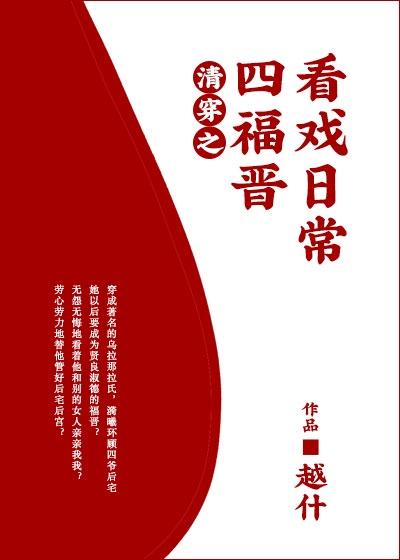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碎玉 > 第 15 章(第3页)
第 15 章(第3页)
堂倌引他们至其中一间,里面一间有一个人在等候了。
来人眼窝凹陷,鼻若鹰隼,是个胡人。
他对着齐楹说了句胡语,齐楹拍了拍执柔的肩膀,示意她坐下,而后亦用胡语作答。
酒肆临街,窗下是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执柔只懂一两句胡语,因而听不懂他们二人的交谈,便静静地望着窗外发呆。
好在他们的对话并没有持续太久,那胡人端起酒杯对着齐楹敬酒,齐楹欣然喝下杯中的水酒,待到那个胡人将酒杯斟满,转向执柔时,齐楹按住了执柔想要端杯的手。
“内人不擅饮酒。”他笑着用胡语说。
这句话中,执柔只听懂了妻子这两个字,她抿着唇只作不懂,耳垂却又渐渐发烫。
离了酒肆,他们重新上了马车。
“不好奇我们说了什么?”齐楹问。
“一点点。”执柔倒是坦诚,“我们和北狄打了许多年的仗,哪怕到现在还时常起龃龉,陛下为何会在这时候见一个胡人?”
齐楹对她的坦诚并不讨厌:“哪有什么敌人。他是个胡商,我在同他谈生意,是要买他们的战马。”
看得出今天的生意谈得很是不错,齐楹难得有这般心情外露的时候。
“余下的时间都是你的,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执柔对京城并不熟悉,因此凝眸思索片刻,却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思来想去,她所熟悉的不过是未央宫罢了,她早已被飞檐翘角的四角天空困住了。
尚来不及说话,只听得一身低沉的马嘶,马车剧烈抖动了一下。
执柔掀起车帘,只见眼前白光一闪,一个蒙面的黑衣人正将刀猛地刺入一个路人的胸前。
鲜血飞溅,以一种夸张的势头喷涌而出。
街上立刻乱了起来,尖叫声、呼喊声不绝于耳。
车夫立刻将发生了什么一一禀告给齐楹,而后抖动缰绳想要离开此地,马车向前走过数步,执柔突然猛地拉住齐楹的手臂:“陛下!我想救他,他还活着!”
鲜血自那人的口鼻涌出,他意识涣散,双手却不自觉地在虚空处抓握着。
执柔收回目光,再一次攥紧齐楹的袖摆,声音愈发急切:“陛下,我若再不救他,他就真的要死了。”
“他当街遇刺,或许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你也要救他?”
“是。”执柔的声音微微发颤,“我母亲通医术,也曾将医术传授与我,请让我救他,陛下。”
“去吧。”齐楹如是道。
执柔如蒙大赦,猛地起身,尚不等车夫将车凳放好,已然跳了下去。
她扑到那人身前,先去掀他的眼皮,而后飞快地解开发带捆住他尚在出血的血管。
身边渐渐围了三三两两的路人,执柔正在拿帕子堵住那人的伤口,他却挣扎着醒了过来,他定定地看着执柔,像是要将她的模样记在心里,口中断断续续:“救我……我不能死……”
“你不会死的。”执柔按住他乱动的手,“听我说,呼吸。”
离她五步远的位置,齐楹亦背对着阳光,静静地站在风里。看不见她的五官,只能闻见风中血液的腥膻。
执柔如水一般的声音穿云破月,如同春风拂过山岗。
第一次听说薛执柔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被太后赐了白绫,几乎没救回来。
再后来,便是在阳陵翁主门前,一个刚死里逃生的人劝阳陵翁主好好活下去。
齐楹知道,这个女人有着世间最柔软的双手,她曾用这双手引他登上青檀塔,此刻亦在用这双手搭救别人的性命。
眼泪不是她的武器,但温柔是。
那一刻,齐楹的心中第一个念头便是:
幸好她活着。
而不幸的是,他却看不见她。
早已习惯黑暗的齐楹,真的很想在此刻看一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