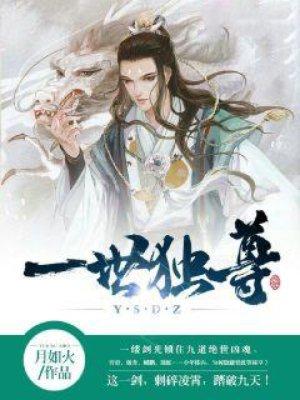墨澜小说>山间柳 > 第156章(第1页)
第156章(第1页)
那两个大汉听后对望一眼,不怀好意地揶揄起他来,
“谁让你自己欠下了风流债,还让人家记恨到非得花钱买你的手不可,我们兄弟俩呢,就只是拿钱办事,你可不要把这事怪到我们头上。”
他们嘴里说着莫怪,神色却格外放松,看起来根本不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抱有负罪感,柳栐言没心思去管这两人究竟是怎么想的,暂时也没法细究这个所谓的风流债到底是从何而来,他咬着话里的几个字,忍不住重复道,
“你们是说…有人花钱买我的手?”
柳栐言弄明白起因,哪怕觉得荒唐无比,也只能先把疑问搁置一边,开始尝试讨价还价,
“那他出了多少,我给你们双倍的价。”
可怜柳医生上下活了两辈子,还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不得不说出这么俗套的台词,他在心里强忍尴尬,偏生这两个罪魁祸首居然一点都不领情,他们上下打量过柳栐言,毫不掩饰脸上的轻蔑,
“还你出双倍,你有这么多钱吗。”
柳栐言心说我可比你们以为的要有钱多了,面上倒还是尽职尽责,尽量扮演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大夫,可他刚想开口再添几句,就被对方接下来的话给噎住了,
“行啊,你要是真拿的出双倍的钱,爷今个儿就发发慈悲,给你留半截胳膊。”
他们好似觉得自己的话十分有趣,说完竟还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柳栐言一言难尽地看着这两人,懒得打断对方针对自己的讥讽,不过还没等他们笑够,就有一道黑影突然从高空急速落下,生生刺进其中一人的脚面,强行将他的笑声梗了回去。
柳栐言下意识低头去看,就见一把通体玄黑的匕首直接穿透那人的脚骨,锋利的剑身全数没入,只剩护手和剑柄露在外头,像根钉子似的将他牢牢钉在地面,迫得这人发出惨烈的嚎叫,柳栐言尚未做出反应,投掷此物的原暗卫已紧随其后,快速落于自己身前,急急唤到,
“主人!”
无比熟悉的声音一经入耳,便使柳栐言终于松懈下心神,向来人借了几分力气,他在对方的护卫中低低喘息,这才发觉自己心跳实在快的厉害,竟是在后知后觉地开始害怕。
柳承午迅速检查过主人的安危,当即被那一大块已经让血迹染透的衣料逼红了眼睛,他目眦欲裂,翻涌而出的杀气几乎在瞬间失去控制,如有实质地威慑四周,柳栐言心里一惊,赶忙伸手拽住这人衣领,忍着周身的疲倦下令到,
“承午,留活口,他们背后有人指使。”
柳承午被主人阻拦,总算因此恢复了些许理智,他勉力咽下喉咙里的血腥气,低下头应了声是,
“属下明白了,主人稍候。”
他在主人面前乖顺的不行,但等转过头时,眼中仍是化不开的瘆人的阴冷,使得被他盯住的二人俱是一震,莫名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们未曾看清柳承午是如何出现的,现在见他向这边走近,心中恐惧就攀升的更甚。
其中被钉住的那个强忍剧痛,急切地想将匕首拔出来,不曾想那玩意就跟钉死了似的,他半蹲之下又难以施力,一时竟无法动摇分毫,于是干脆握住长刀,准备在柳承午近身时下手反击。
可他气势汹汹,却明显低估了原暗卫的敏捷,柳承午身形刚动,下一刻便从二人的视野中失去踪影,他转瞬来到男人身后,朝着对方微曲的膝盖狠踩一脚,那人就受力跪下,使得足弓被迫弯起,反倒主动迎上了匕首的刀刃,令那伤口顺着力道撕扯的更深更长。
男人伤上加伤,立刻疼得满头是汗,然而还没等他喊叫出声,就被柳承午用力击打于后颈,顿时眼前一黑栽倒下去,横躺在地上没了声息。
另一人看同伴落得如此下场,哪里还不明白这次是踢到了铁板,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物,他无心恋战,只想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结果踉跄中还没能跑出几步,满是破绽的后背就骤然一疼,却是柳承午换了一柄短刀,沿着这人右侧琵琶骨的边缘刺进,精准地从肋骨之间的空隙穿过,全无阻拦地直直扎入肺中。
男人本就失了战意,遭此重创更是溃败,柳承午一击即成,又不愿为他们浪费多余精力,便如法炮制,以手为刃将其劈晕,转而回到主人身侧。
他满心惦念的都是主人伤势,于是力道用的极重,生怕在这等闲杂身上多耽搁一点时辰,只是柳栐言看那二人昏在院里,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还担忧他们会找到机会逃跑,犹豫要不要先将人绑起来关好,柳承午在一旁焦急的不得了,忙道自己手下有数,短时间内定是醒不过来的,就是真的醒了,也不会任由他们脱身,这才哄得主人放下心来,随他进入屋内处理伤口。
柳栐言先前忍得久,本已感觉有些麻木,但等柳承午低声告罪,替他小心剪开衣袖,再次瞧见那些浸染在浅色布料上的、已经变成暗红色的大片血迹了,反而又记起疼来,错开眼睛不敢细看。
而与他相反,柳承午则死死盯着主人的手臂,接近自虐般的,发狠地紧咬住了口中的软肉。
他在过去受过无数伤,吃过无数苦,但却从未像现下这般惊惶,发觉利器竟凶狠至此,能轻易伤害到他的主人。
作者有话说:
流水账写手为了这段勉强算是打戏的打戏想到头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