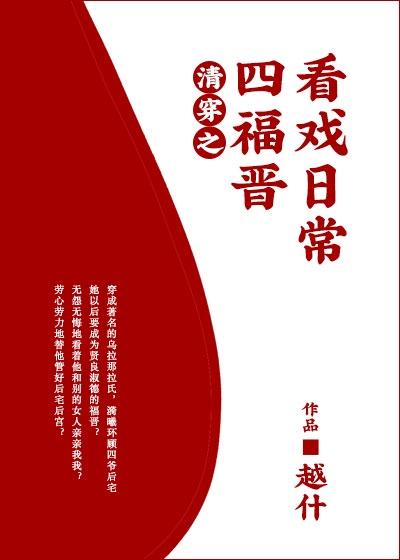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初唐异案 > 327 其言也善(第2页)
327 其言也善(第2页)
张易之、张显宗将武后指明的三首诵读完毕,看向卧榻上的武后,原以为她已然入眠,谁知对方眼神炯炯,望向兄弟两人一侧,“朕所作此《唐享昊天乐》十二首,是为证自身较他人,更当为一国之主……”
“如今夙愿已成,至今过十余载,眼看将是油尽灯枯之时,此其三、其六、其九三首,便是朕终末之时,留于……世间诸人一件要物,许朕凭此,保不准可得长生,亦未可知。”
“汝二人,务必记住日日吟诵数遍……”武后当时满脸即有对二人说明之意,但终还是无力地委婉笑笑,“朕之寿如何得就完,汝二
人只记得于此迎仙宫内,凡朕清醒时,不时诵读此三首予朕听,保不齐,”武后虚弱至极地笑笑,“汝二人他日若遇险,救赎之道,亦于此三首诗中。”
翠峰山上,夜晚凉意已去,晨光尽至,武三思、韦巨源只觉身上炭火之气,渐渐由阳光暖意替代,这时韦巨源所提之问,终有个解答。
就在武后所言张易之、张昌宗“救赎之道尽在诗中”后,不几日,御医便察觉武后喉管尽是浓痰淤积,莫说言声,只论不及时将痰吸出,连呼吸吐纳都将受阻。
“姑母说于当今圣人那番遗言,若非回光返照,恐亦难留下些许字句,”武三思摇了摇头,“可怜那张氏兄弟二人,只差一日,命便不得改动,却咎由自取,惨死于五万一众之手。”
“依殿下所言教,先皇则天大圣皇帝于张氏兄弟二人之遗言,莫非就只是每日诵读《唐享昊天乐》三首?”
“言语还有些其它琐碎,但依他二人前来我府上所言,唯有此一番话算得是正经遗言。”
“望请殿下恕下臣愚钝,只凭此一番话,三首诗,如何拼凑出先皇则天大圣皇帝改葬之处?”
“韦相回想得精巧,”武三思戏谑地看了韦巨源一眼,抢过话把,“本王早先言姑母下葬另有别处,汝此刻提及,正是本王欲韦相相助一解之惑。”
“下臣何德何能!?殿下及一族思索这许久,都未能解,下臣如何……”
“嗳!韦相如何自薄至此!”武三思起身,迎面向晨光,“方才韦相所言‘拼凑’,本王一族只将组诗中三首联系至时日、所在、其人,却未曾想过其诗之中,或有其它线索。”
韦巨源本无此意,然经武三思此言,又不便否认,一时语塞。
武三思反倒有些激奋,继续说道,“张易之、张昌宗觉自身走投无路之际,才至本王府上,故而本王格外在意,以至于姑母终末一日,本王还留意起兄弟二人求助前,提及过之姑母临终所书一张字纸。”
“方才想是错过听得殿下言及此事,敢问字纸其上所书为何?”
“方才本王亦未言过,字纸所书仅三字,歪斜扭曲之至,书有‘三、六、九’……”
“仍为‘三、六、九’?”韦巨源之诧异溢于言表。
“姑母反复提及此三数,岂非重提《唐享昊天乐》组诗?”
“既已病入膏肓,岂有再提几首碎诗之理……”韦巨源不敢讲此言声张,转而另作他言,“倘若仍重提组诗其三、其六、其九三首,若非诗中藏有何密辛,亦不得将其作而为驾崩前最后一手手书。”
“组诗……不得言却强行……”
武三思回忆当日武后驾崩之时,自御医处听得的异况,武后是如何自嗓中,对当今圣人硬挤出几句遗言,而最终一句竟是“禅机已到”。
“当今圣人,乃姑母第三子……组诗第三首,岂非就于此玄元皇帝庙所
作?”
武三思一脸恍然开悟,“‘禅机’已到,岂非对当今圣人所言,而是以张氏兄弟二人仍于迎仙宫中侍候,于他二人所言?”
“弥留之际,缘何偏再于他二人交代事项?真应了那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则组诗其六一首与其九一首,所为又是为何?”韦巨源再度彻底陷于难解之境。
就在两人各有所思之时,家奴自下方玄元皇帝庙处奔跑而上,直站定于武三思、韦巨源身前,上气不接下气。
“作何模样!?”武三思怒喝道。
“禀……禀殿下,山下……”家奴气喘不止,“山下有一行人正往山上来?”
武三思一惊,大声回问,“可看明是为何人?”
“未……未曾看得清楚,”家奴一脸惧色,汗珠不断向下掉,“只是一行足有数十人,还有兵士与武侯……”
韦巨源也同样站起,向全然看不见的山下望了一眼。
“城中这般状况,能往此山而来的,又能是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