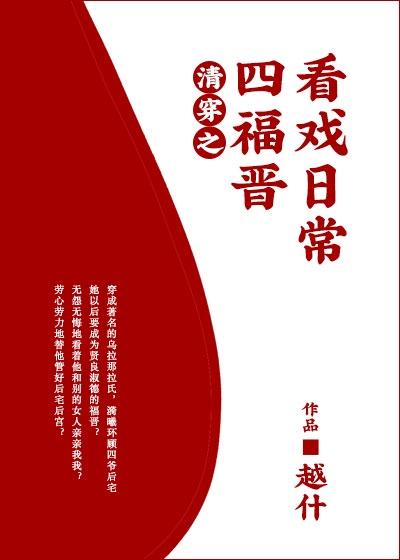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初唐异案 > 327 其言也善(第1页)
327 其言也善(第1页)
神龙元年正月月初,年迈之武后夜中偶经风寒,便再难起身,终日竟连卧榻都难走下,只得长卧于榻上,由御医看护调理。
因不愿将已自觉深重之病情,过早暴露于其他人前,她宣召太子独自监国,自己退于迎仙宫听政,将一众朝臣皆拒于门外,且吸取前一次张氏兄弟二人协助监国,险酿大错的教训,此一回将兄弟二人留于身边。
若前一回,张氏兄弟二人对武后身体康健、尚得执政百年多有妄想,此一回于武后卧榻前,见其形容枯槁、精气涣散,甚于往日往次甚多,便知此一回或回天乏术,只想着自己眼前该如何活下去了。
此一番想法甚有些道理,武后就算此时未发重病,其大寿终至风烛残年之时,寝宫之外的紫微宫别处,皆有虎视眈眈之目光紧盯着迎仙宫内的动静。
且兄弟二人早听闻有风声,彼时桓彦范、袁恕己之流,已然伙同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李多祚、李承嘉、宗晋卿等人,静待时机谏言,将武后尊为太上皇,而使她让出皇位,由当今太子继承大统,恢复李唐皇制。
张昌宗性急且鲁莽,少不得此时与阿兄合谋,以武后命不久矣,自己兄弟二人往日造下的罪孽或将遭报应为由头,再三说明当先下手为强,剿杀太子与其一众拥趸。
而张易之亦感灾祸将至,知二人哪怕欲收手,向太子一众服软,也已不得成,思来
想去,拿定了与其畏首畏尾不敢决断,不如放手一搏的主意。
策划政变,首先当是人手——张氏一族因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得武后爱宠,鸡犬升天,短短几年便于东都之中壮大成了相当势力。
朝中文武之中,亦有相当人数或被收买,或为兄弟二人之势威逼,总之若要以实力论,或许勉强可凑出一支挟病重武后,而逼迫他人屈服之军伍。
如此一来,大权依旧在握,只需再从无论武氏或李氏皇族之中寻得一名年幼傀儡,受武后钦命继承大统,由是至少能再统管一国些许时日。
到时无论想要全身而退,逃往其他藩国属地,或是请国君予自身免死,都还可从长计议。
他二人盘算得周全,却难敌武后于此将魂归天际之时,对他兄弟二人另有安排。
是日,武后将他二人唤于卧榻一侧,说起一件旧事,确切些说,说起一组旧诗。
兄弟二人曾为讨她欢心,时常于聚众欢愉之时,大庭广众之下,选其中几句高声吟诵助兴。
而这时被武后唤于其身旁,竟亦是让兄弟二人同过往那般,选彼时一十二首《唐享昊天乐》中朗朗上口的,来吟诵。
兄弟二人自不解其中何意,但又苦于哪怕决定要反,也要借助此时武后之威,只得从虚弱之中这位武后之命。
虽说采选其诗,但两人岂是终日执武后所作诗句而不放手之人,才背下熟悉的几句,即为仰卧于榻
上的武后打断,“还是取来诗集,照本念罢。”
张易之不敢忤逆,向内侍要了集子,转而朝着武后问,“陛下愿听哪一首?”
此时的武后未有那般清楚意识,吐纳时而悠长,时而短促,只报出几个数字,“其……其三,或六,或……九。”
张易之、张昌宗不知缘何是为此几数,但就算武后已然神志不清,她之所言仍为不得不遵守之口谕、旨意。
高宗驾崩后,武后欲取李唐而代之之心尽显,但又不得不暂时顺应一众老臣口中之“延续李唐血脉、继承先皇遗志”。
故而于她个人而言,处境甚为逼仄烦闷,满心建国之志,又处处受阻,若要放手不管,又舍不得一路铺垫而来之成果。
在这般状况下,唯有同以延续先皇遗志为由,将自己一番打算融入其中,再向群臣借势说明往年往日临朝之时,武后甚为二圣其一,有多励精图治,又有多忍辱负重。
武后文采寻常,甚可称不堪一提,然十二首《唐享昊天乐》其中对高宗的追思与不吝赞颂,倒也受到了一群固执己见之老臣的认同。
这番认同对日后武后称帝,取李唐而代之,或多或少还是起了些许效用。
十二首《唐享昊天乐》,每一首都较前一首补足武后为李唐所治之症及所立之功。
以其三而言,“乾仪混成冲邃,天道下济高明;闓阳晨披紫阙,太一晓降黄庭;圜坛敢申昭报,方璧冀
殿虔情;丹襟式敷衷恳,玄鉴庶察微诚。”
不论其中哪一段,遣词造句皆生硬晦涩如上古文书,而诗内所述,不过是一番于高宗、于自身的夸耀,之外便是自己对治国的一片赤诚。
再如其六,“昭昭上帝,穆穆下临;礼崇备物,乐奏锵金;兰羞委荐,桂醑盈斟;敢希明德,幸罄庄心。”
初唐善诗之人无数,若皆存至武后所作此诗之时,不知将作何感想,但诗中之意就同武后那颗溢于言表之司马昭之心,似在世中借向天地证明自己当有一国之主之姿,而证于群臣之前。
至其九,则大有心愿即刻将成之相,“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庙略静边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资先化,无为遵旧矩;祯符降昊穹,大业光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