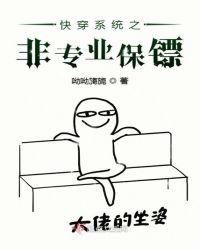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书剑游侠传 > 第五百五十四章 边声四起唱大风(第1页)
第五百五十四章 边声四起唱大风(第1页)
“嘿,你这酒疯耍起来,惊天地泣鬼神,痛哭流涕,恨不得以头抢地,哭得我在旁阵脚大乱,不知所措,只能把你哄睡了,再偷偷跑掉。”薛靖七弯起一双笑眼,添油加醋,无中生有,神色却正经得不行,愣是把他听得瞠目结舌,怀疑自己压根不是喝醉了,是中了毒吧!
“可我,毫无印象。”易剑臣严肃地皱起眉,回想。
薛靖七双眼微眯,冷笑一声,抬手不轻不重一敲,赏了他个清脆提神的脑瓜崩,玩味道:“你不是醉死过去记不清了么,我这么个老实人,还能骗你不成?”
“其实,大多细节我都记起了,包括我抱着你有点难过,许是哭了,只有……最后那件事我记不清了,我应当,守住了吧?”易剑臣柔声解释着,说到后面,脸又微微红起来。
“……?!”薛靖七听闻此言两眼一黑,天爷,怎么又绕回这个话题了,怔了一瞬倒吸口气,一脚狠狠往旁踩去,易剑臣猝不及防被攻击,“嘶”的一声吃痛,倏地躬身跳起脚,旋即又被前者抬臂曲肘揽过,一把勒住脖颈,咬牙切齿道,“老子再说一遍,不准回想昨夜!”
她凶巴巴说这话时,温热鼻息同身上清冽的草木香一齐扑到他面上,迫得他根本定不下心神,耳根滚烫更甚,悄悄抬眼瞥她,喉头一滚讪笑道,“阿靖,我错了,你别生气。”话音刚落,没等她回神,又蓦地倾而前趋,偷袭似的在她鼻尖轻啄一下,吓得薛靖七猛然挣开窜出老远,横剑在前,结巴道,“过分了啊,媳妇你,能不能冷静下。”
易剑臣伸手摸了下鼻尖,抿着唇,似是意犹未尽,抬眼望她,眼眸清亮如新磨水洗过的刀,笑吟吟道:“我挺冷静的,很克制了。”
这,这家伙脸皮真是越来越厚了……厚如三尺城墙!
罢了,好夫君不跟媳妇斗。
薛靖七垂眼静默片刻,抬手又紧了紧衣领,锁骨旁的红印子是遮住了,颈窝处实在无能为力,索性长叹一声,不再去折腾这事,手中剑鞘一旋倒扛肩上,眉头轻蹙,若有所思地踱到他跟前,挑眉道:“诶,说正经的,剑十九,你练过没?”
不出她所料,面前人笑意渐隐,眼里的光一闪而没,沉入水潭,整个人从明亮狡黠褪作清峻沉郁只需要“剑十九”三个字。
他没有答话,捏住剑谱的手指紧了紧,骨节分明。
“难道,我们看见的东西,不一样。”薛靖七见状叹了口气,另一只手轻轻盖在他持剑谱的手上,又用力攥紧,想了想,故作自在地极轻一笑,抬眼注视着他躲闪的眸子,认真问道,“你看见的是什么?不会是我的尸首吧。”
易剑臣变了脸色,情绪陡起波澜,死死盯住她正欲说些什么,却被抢白。
“你看错了。”她坦然迎上他的目光,拇指安抚似的摩挲了几下他的手背,一双笑眼弯成月牙,笃定道,“我看到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一切都会结束,我也不会死。真的。”
他眸光闪烁,怔在那里心乱如麻,张了张口,却说不出话。
“千真万确。”薛靖七再次拖腔拉调重复了一遍,见他依旧是那副怔忪模样,哑然失笑,踮起脚仰首凑前,小鸡啄米似的在他唇边迅速碰了下,一脸讨好,“你啊,关心则乱,总是喜欢胡思乱想,自己吓自己。我猜,你根本就没认真看过剑十九,估计看了一眼吓得立刻扔了,是吧。”
易剑臣有几分动容,垂下眼,也不知信与不信,身子总算没有方才那般紧绷,长长吐了口气,默不作声地抬臂圈住眼前人,一手揽腰,一手抚颈,下颌抵在她肩膀,许久之后才轻轻“嗯”了一声。
薛靖七安静地靠在那里,抬起一只手轻轻在他脊背处摸了摸,持剑的手垂在身侧,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眉头轻蹙,颓然闭上双眼。
她也不知,她这般骗他,究竟是对是错。
其实她什么都没看见。
只在这一剑的剑意中,感受到一片死寂的黑暗,漫如长夜,半点微光都寻不见。
可是没有恐惧,没有痛苦,没有悲伤,甚至没有孤独,如一滴水沉入海,波澜不生,倒有些……清冽澄明,从容赴死的味道在其中。
她隐约明白此剑何意,心境却无从寻觅,为最大限度接近剑十九之意,她熬至下半夜以黑布蒙眼练剑,在无边的黑暗中挥出每一剑,从头至尾练上几遍,总是拿捏不准,人剑能合一,心剑却难合一,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纵然一剑能断风、分云、斩尽山上雪,却终究不是真正的剑十九。
只能理解为,一切自有定数,时机未到,尽人事也无用。
倒不如真心实意地及时行乐,落拓不羁,快意余生。
可易剑臣向来不是能想得开的人,跟他摊牌是不行的,只能骗,能骗一时是一时,骗得他宽下心来能痛痛快快过完接下来的日子,应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