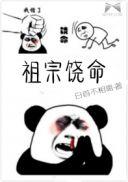墨澜小说>月亮淋了雨 > 9赌王(第1页)
9赌王(第1页)
病房外有几棵松树,栽了很多年,已经长得又高又茂盛,树影在窗户上摇曳,如同此刻病房里祝矜起伏的心绪。
她问邬淮清,他是否还记得今天下午她在派对上和他说了什么。
邬淮清握住手机的一个角,然后把它在空中打转儿,漫不经心地思索着。
片刻之后,他说:“我又不是金鱼,不会那么快忘记。”
是,他不仅不是金鱼脑,还记忆力特别好,对数字过目不忘。
祝矜经常怀疑他的脑子中每天装那么多东西,不累吗?
“你既然还记得,那你就不能在这儿。”她闷声说。
邬淮清挑眉,“为什么?”
祝矜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把口罩往下拉了拉,又想起脸上过敏的痕迹,重新把口罩戴好,“你现在在这儿,我怕你女朋友来打我,那么多,我可招架不住。”
邬淮清忽地笑了,他吊儿郎当地说道:“放心,她们忍耐力好,多你一个不多。”
“正好,来了还能凑几桌麻将,给你解闷。”
“……”
祝矜看了他三秒,然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决定不再和他说话。
谁知他继续说道:“哦,我忘了,你不会打麻将。”
祝矜睁开眼睛,立刻反驳:“谁说我不会的?”
一双杏眼瞪得圆圆的,邬淮清被她的模样给取悦,想起之前过年时,大家聚在一起打麻将的情景。
那会儿祝矜还读高中,大家还都住在大院儿里,没有搬家,过年的时候最是热闹。
除夕夜,他们小辈聚在一起,在宁小轩表姐家,躲着大人打麻将,祝矜不会打,就在祝羲泽旁边干巴巴望着。
看得手痒,她也想打,于是宁小轩他们说要教她。
谁知祝矜平时看着挺聪明的,在牌桌上偏生缺一根弦,怎么也记不住规则,记住了又不会用。
教到最后,连宁小轩自己都被带得懵了,求爷爷告奶奶让她赶快下桌:“浓浓,哥求你了,哥刚赢的都归你,你快下桌去吧。”
祝矜看着一桌子看她好戏,想笑不敢笑的人,连祝羲泽都在笑,她哼了一声,一个人去沙发上看春晚。
那天,邬淮清春风得意,赢得最多,讨了个新年的好兆头。
他转过头一瞥,正看到小姑娘正坐在沙发上嗑瓜子,春晚上不知道在演着什么小品,她不时笑出声,一双眼睛笑得弯弯的,和月亮似的。
和刚刚下牌桌时愤愤不平的模样截然不同。
那会儿他在想什么?
琢磨她为什么总能那么开心,所有的不开心,都跟云烟似的很快散去,身上从来透着一股被宠爱长大的劲儿。
宁小轩闹着要邬淮清明天请客。
祝羲泽说,大年初一都要去拜年,哪有时间一起吃饭。
于是宁小轩又给邬淮清安排上,让他初八的时候请他们一伙人去鸿彦楼吃,鸿彦楼很贵,反正这竹杠他是敲定了。
不待邬淮清应下,宁小轩又连忙喊沙发上的祝矜:“浓浓。”
“咋了?你把钱输完了?太好了。”她转过头,说着拍了拍手。
“……”
宁小轩又气又笑,说:“是没剩多少了,都被邬淮清赢走了,你淮清哥说了,初八要请大家伙儿去鸿彦楼吃饭,你那天记得空出来。”
祝矜看向他,眼睛在灯下滴溜溜转,邬淮清手里拿着一麻将牌,任她打量。
那眼神不是很善意,好像她不会打麻将,都是他造成的,所以他才能赢这么多。
这副麻将是宁小轩从他表姐这儿偷的,是某个奢侈品牌跨界出的,一套就要十几万,手感很好。
他握在手里摩挲,半晌,听她淡淡地说:“再说吧,好多同学约我出去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