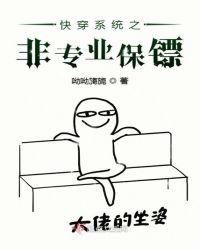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万里踏莎行 > 出使宋营(第2页)
出使宋营(第2页)
明新微打断道:“对了,钟官人不会以为我山中就只有那几员猛将吧?不怕与钟官人你交个底,就最后斩杀济州团练使的那位将军,我山中就还有数百。若是不信,只管来试试。”
兵不厌诈,立安山里哪来第二个杨束那样的神兵?又不是话本演义。
钟为盏想到被那人当胸贯穿斩于马下的济州团练使,心有戚戚,竖立的眉毛胡子逐渐耷拉下来,口中仍不服输:“举国多少将才,还能怕了你小小立安山不成。”
明新微说话听音,立马循循善诱:“何至于要倾举国之力?我在双方伤亡未重时来谈,为的便是把这诏安的功劳送给钟官人,若不如此,等战线拉得久了,三司拿军费参你一本,换了别人前来,钟官人岂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钟为盏心中一动,听她道:“我朝历来以和为贵,为此不惜每年给北辽三十万岁币,好在这钱花得也值,过去十几年来,百姓总算得以休养生息。只是在这期间,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后土,造玉清昭应宫供奉天书,虽没打仗,花费也不少。天禧年间,黄河几度决口,各地蝗灾四起,又有风雹害稼,须发廪振灾,甚至贷为种粮,前有夔州饥民要均分土地,后有贝州弥勒教兴风作浪。再看这全国上下,水利、马政,哪处不要钱?辛某僭越,帮三司使厘算了一笔账,看看是诏安立安山好,还是兴兵讨伐好,钟官人不妨参考参考。”
说罢,明新微贴心的为钟为盏递上了一卷手札,免得这位老臣年老体衰,过耳即忘,又无文书随侍左右,漏了些要点,那就不好了。
明二哥见钟为盏似被说动,怕夜长梦多,连忙上前帮忙接过手札,转呈给钟为盏。钟为盏眯着双眼迅速扫过手卷,虽没说话,却一招手,把文书递给了一旁的老书吏。
明新微心下一松,成了。
明二哥见缝插针,主动道:“恩相,不如由末将护送来使出营。”
于是明二哥并两个统制官,一路护送明新微出了宋营。庞秀安排的接应人马见了,连忙迎上前来。
明新微便冲明二哥行了一礼道:“多谢这位将军相送,我突然想到,船上有给钟官人备下的一份心意,不知是否方便转交。”
她打了一个眼色,身后的立安山小卒便立刻上前,各自拿了贿赂,塞到那两位统制官手中。那二人对视一眼,拿在手上掂了掂,会心一笑。
明二哥便装模作样点点头:“转交可以,钟官人收是不收,我就不能保票了。”
“那是自然。”
明二哥便跟在明新微身后,上了立安山的船,一路进了窗户紧闭的舱室。
他栓好门,转过身来,就见妹妹立在舱中,高了些,瘦了些,穿着陌生的绣衫战袍,近一年未见,好似变了个人,又好似一点没变。
她冲他露齿一笑,笑着笑着,眼圈渐渐红了。
明二哥只觉千言万语堵在胸中,喉头一哽,张了张口,没出声,跨步上前,抬手把妹妹的头摁到胸前,半晌,才涩声道:“怪二哥没用。”
明新微轻轻推开明二哥,指尖飞快在眼尾一擦,拉起他的手臂:“当初我走后,你在寺里后来又如何了?家里又如何了?当初受的伤,可好全了?”
“你一口气问这么多,让我先回答哪个?”明二哥笑了,拍拍她的手,“伤早好了,一点疤也没留!家里也一切都好。”
“家里怎么个好法?你当初脱困后,回去是如何说的?后来陈籍找到你,又是如何说的?你快一五一十,把事情都从头道来,不然我得急死。”
“家里那点儿家长里短的事儿,什么时候说都不打紧,倒是你……”他说完紧紧盯着妹妹,不敢错过丝毫神色变化,小心翼翼问道,“倒是你,落入土匪窝里,可有受什么委屈?那个纹了青色狼头的呢?可欺负了你?是何名字,我定在战场上取他首级!”
明新微听他说“家长里短”,便知晓估计是老家的人有些微词,但想来爹爹应当应付得来,如今时间宝贵,倒也不必刨根究底地细问。
她又观明二哥神色,猜到他心中所想,为宽他的心,便微微抬起下巴,露出几分骄矜的神色:“你看如今天下扬名的辛明先生,像是在立安山受人欺负的样子吗?”
明二哥半信半疑,不放心地问道:“那刚上山呢?他们当初抓了你去,总不会是缺军师吧?你别怕,二哥定会为你报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