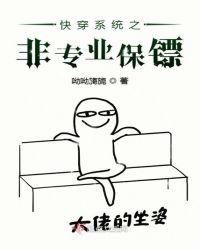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万里踏莎行 > 出使宋营(第1页)
出使宋营(第1页)
六月末,明新微女扮男装,以使者辛明的身份,去往宋军军营。
若是为了显示气度,她本该穿一身文士袍。但一来她没有相应的公服可穿,二来铠甲能够显得她更魁梧一些,正好掩盖女子的身姿,最后便作了「衷甲」打扮——铠甲外罩绣衫短袍。在重文轻武的大宋,也有武人表示恭谦的意思。
福云带着秋珍冬珍,连夜改制了一领贴身铠甲,并在广袖短衫上绣了踏云瑞马。
使者辛明,就穿着这样一领簇新的战袍,来了宋军中军帐。
刚一进账,明新微便在左列小将中,一眼看到了明二哥。野寺一别,再见却难相认,兄妹俩各自转开目光。
她冲着对方的主将行了一礼:“立安山辛明,代庞秀先生,特来一晤。”
大宋历来是文臣统军,此次派来的时枢密副使钟为盏,年事已高,眯着昏花的老眼,伸长脖子:“哦,你就是辛明?是你写的檄文?”
“正是。”明新微不卑不亢。
“哦,可惜了的——你这后生,文采不错,脑子不够灵光。”他晃了晃脑袋,幞头上的两个飞天幞脚也跟着颤了颤,“太平盛世,不做天子门生,偏去做天子贼人。”
明新微垂着眼,一眼便看到这老官人的曲领大袖上有一块油污。不修边幅的老学究钟为盏,往年明家送他的年节单子,她都有看过,知晓此人最爱故纸堆,凡事并不出头冒尖,擅长和稀泥,但也勉强算个不群不党的纯臣,不知此次为何竟然叫他领军,她想,也好,正中我下怀。
她半点不觉得自己是“天子贼人”,大大方方道:“钟官人此言差矣,我们立安山同天子没有半分的过不去,相反,比谁都希望官家稳坐这江山,这才冒着杀头的风险,当头棒喝,刮骨疗伤,说是纯臣也不为过。”
作乱的贼子,竟然自比“纯臣”,钟官人顿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花白的眉毛胡子一齐抖动起来,怒道:“一派胡言!水贼草寇,也敢妄言忠义,可笑至极!”
“可不可笑,不妨听我说完,再做论断。”又行一礼,她慢声道,“从太宗到真宗,再到如今的官家,钟官人是三朝元老,历经战乱,也治过太平,见识想必远在我等草寇之上,不知钟官人观我大宋江山,眼下最为紧急之事,是何事?”
钟为盏自然不会回她的话,余怒未消,拿鼻孔看人。
“想当初太祖立国,乃是从后周孤儿寡母手里继承的江山,深知幼主治国的弊端,这才有了后来金匮之盟,不传其子,而传其弟太宗。”
这话说得讽刺,一口一个“孤儿寡母”,一口一个“继承”的,说到底,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算不得多光彩,趁着旧主尸骨未寒,把七岁的后周小皇帝柴宗训赶下来,自己当了皇帝。这位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确实会捡,随手一捡,就“捡”了个大宋江山。如此便宜,让多少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枭雄看了,不呕血三升?
钟为盏听她言辞间对太祖不算太恭敬,有心想维护两句,但毕竟是太宗朝的老人了,一时没想好言辞,只又听她嘚嘚往下说:“可如今不过几十载过去,大宋兜兜转转,竟又轮到幼主继位,当今官家的险境无须多言。”
她大义凛然道:“我等所求不多,只求太后不行武曌之事即可。”
钟为盏在朝堂上打了一辈子太极,从太宗朝和稀泥到真宗朝,太后和端王明里暗里斗法,他自岿然不动,还没同谁如此当面锣、对面鼓地打开天窗说过亮话,此时听了如此赤裸裸的言辞,舌头打结,一口气不上不下,干瘪斥道:“无稽之谈!太后深明大义,岂会做此背弃祖宗家法之事?临朝议政,不过一片慈母爱子之心。”
明新微双眼一亮,打蛇随棍上:“若太后能明诏自证,我等即刻止兵休戈,俯首称臣,但凭驱使,绝无二话!”
钟为盏花白的胡子一翘:“简直放肆!一国太后受水贼所胁,传扬出去,岂不贻笑大方!”
“欸,谈什么胁迫不胁迫的,岂不见外?在下观你我双方俱是忠心大宋,只在细枝末节处有所分歧,既然都是一片忠心为了官家,相煎何太急?钟官人何不代为传话,成就一番诏安美谈呢?”
“哼,诏安?区区水泊,我虎翼军顷刻便可踏平,何须如此麻烦?”
明新微见状,便袖了手,也不再相劝,故意露出几分倨傲:“是吗?不是在下夸口,就凭阁下军中这点人才,便是侥幸登上虎头滩,也只能在山脚下做了断头的鬼。”
“济州城下一番搦战,想必你也见识过我军中几位虎将,个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加上山道数道关隘,保管让诸位水军,有去无回。”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