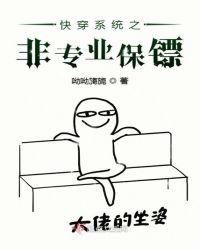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女国公 > 100120(第37页)
100120(第37页)
而现在,她要将这些天打她、踹她的东辽狗全部拖出来,把他们的肉一刀刀割下来喂鹰。
没有随军大夫,虞归晚也不知幼儿是否受了内伤,问她也也不肯说实话,再就摇头。
“我身体没大碍,”幼儿被她从马上抱了下来坐在缓坡避风的地方,脸色虽有些不好,但精神尚可,不想她为自己担忧,有些事是万不可在这种时候说的,“前头的战况要紧,你别在我这里耽搁,快去。”
她头上的伤处理得很粗糙,口子还狰狞着,可见当时那伙人下了多重的手。
虞归晚没动,只是抬手小心碰了碰她的脸,一点劲都不敢使,还担心自己手上的茧子会刮疼她。
“这里没有好大夫,待这的事收了尾,我便带你去偏关小镇找大夫,先清理好头上的伤口,养养身子再启程回南柏舍。”
她再不放心将幼儿交给任何人,总要在自己能看得到的地方才觉得安心。
她也不会那么快回河渠。
伤了她的人,妄图霸占她的地盘,可不是死二三十万兵将就能结束的。
她一定要让傀儡军出关,让东辽也尝尝被提上砧板任人宰割是什么滋味。
早之前她就做过关外地形的沙盘,商道图也有,原是为迁居关外草原准备的。
既然现在不打算去了,那就把关外的地盘划到庶州来,都归她,谁都别想跟她抢。
她执拗起来,幼儿也无法,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可到底记挂着廖姑,又催促虞归晚快些下去救人。
“她伤得重,现在也不知怎样,万不可再落到刘卜算手里。”
经她一提,虞归晚又想起刚才营门前那东辽女人说的蛊毒,就问幼儿,“说你中了蛊,什么意思?是不是她给你喂药了?”
在末世她见过基地的研究员给人注射药物,什么类型的都有,最后结果当然也不会太好,那都是实验阶段的药物*,药性不稳定,后遗症严重的还会致死。
她刚才就是察觉到幼儿不对劲才刺破那个拨浪鼓,她知道幼儿肯定有事瞒着。
幼儿还是否认,“没有的事,别听那种人瞎说,她就是故意的。”
“是吗?”虞归晚并不信,她深深看了眼幼儿,随后站起身,“我先下去,很快回来。”
她要亲手抓刘卜算。
幼儿满眼不舍的看着她上马离开,直到连背影都看不见了才收回视线,注意到守在缓坡上的猛兽跟以往看到的不同。
妙娘从远处赶过来,上下看了她好几遍,才一屁股坐到地上说:“真是把我给吓死了,原以为送你去县城能安全些,谁想竟出了这事。”
幼儿偏头咳了两声,“你可别在岁岁面前提这事,我怕她心里难受。”
“就算我不提,虞姑娘也不好受,她挺自责的,觉得是自己没有护好你。从你被带走那日算起,她嘴上是一句不说,脸上也瞧不出什么,但我们这些跟她比较久的人都知道她心里怎么想,她这回是真生大气,要发大火了。”
幼儿看着下面快要被大火烧毁的东辽大营,什么都没说,心里却是畅快的,庶州百姓受的苦楚,现在是该跟东辽清算了。
第120章第120章
在东辽占领偏关的这几个月,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边民百姓的生活形同水火。
在大营附近还有数座尸骨垒起来的‘筑京观’,哪怕深秋露重天寒,气味也不好闻,而垒观用的尸骨就是之前战败的北境军。
东辽人还在此圈林围猎,猎物非野兽,而是大营中的奴隶。
这当中大部分为边民百姓,亦有关外草原的牧民,东辽人将他们赶到猎场,像对待牲口一样驱赶他们,以猎杀他们为乐。
如今身份调换,黑鹰盘旋在高空,紧紧盯着从小道逃跑的刘卜算,任她的手下如何射箭都无济于事。
她成了猎物,正在被虞归晚带人追逐猎杀。
能在纳措身边得用,又能在东辽境内掀起血雨腥风,刘卜算自是有她的底牌。
随军出征的部族青壮还有两万人藏在大营后山,随时听候她的调派,本也是作为她保命的后路,她选择从这逃出也是为了引虞归晚入圈套。
傀儡军还在大营奋战,虞归晚只带了程伯等小队人马来追刘卜算。
双方在山谷入口停下对峙。
刘卜算胯下的草原马焦躁不安,似是在害怕对面虞归晚的那匹枣红马。
先前在营门只匆匆几眼,刘卜算就牢牢记住了虞归晚的脸,并兴奋的有些不同寻常,想要招揽的心更加强烈。
现在就远远喊道:“我和你若是联手,拿下东辽和大雍就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到时我们称王称帝,独霸天下,不比现在为他人卖命来得好?我早有此心,就不知你是不是聪明人了,随望京不肯答应,是她不识趣,我看你不是蠢人,应不会如她那般蠢,家人都被雍帝杀了,还想着效忠,呵!愚忠!这样的人最不长命!”
反派死于话多,虞归晚自认不是正派角色,也一向懒得同人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