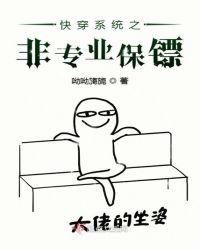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贵极人臣 > 386 时乖不遂玉女愿 再也不会有人那么爱(第3页)
386 时乖不遂玉女愿 再也不会有人那么爱(第3页)
世人就是如此,越易得的越不珍惜,要是难得起来,反而越发心心念念。佛保到最后心里仍然七上八下,却并不后悔,成大事者,就要有敢冒险的勇气。而再糟糕的局面,只要肯用心经营,一样可以化险为夷。
他问贞筠:“夫人为保谢丕的命,甘冒这样的风险,难道也动了再醮之思吗?”
贞筠一惊,她道:“绝无此事。只是恩义而已。”
佛保切了一声,他接着道:“咱家打算将图纸献给义父。”
贞筠又被他惊了一次:“刘瑾?”她没想到,这样的机会,佛保竟然肯拱手让人。
佛保笑道:“太监是无根,又不是无心。这样做,一是全我和义父的父子情谊,聊表我的孝敬之心,一来夫人所求甚大,不得义父首肯,我也不好动手。三来事成之后,夫人能交来图纸那是皆大欢喜,要是不能……”
贞筠一凛:“你待如何?”
佛保笑呵呵道:“夫人莫急,我当然不会拿您怎么样。您不高兴了,李尚书就不高兴,李尚书不高兴了,那皇爷岂能高兴得起来?主上郁郁寡欢,我们这些做家仆就更是坐立难安了。不过,和您有恩义的那个人就难说了。”
贞筠的心沉了下来:“你在威胁我?”
佛保摆摆手:“岂敢岂敢。咱们之间有什么不能商量呢?就算我与夫人没得说,咱家的义父和李尚书总有得说吧。”
贞筠一回到马车上,就不由面带愁思。宋巧姣问道:“夫人,是没谈成吗?”
贞筠长叹一声:“谈成了,麻烦反而更大了。”
宋巧姣不解:“这是何故?”
贞筠欲言又止,当然是因为她也无法解决棉线断头的问题啊。将锭子竖起来容易,只要思路打开,要做到这点并不难。这个主意,就是与林婆交好的女工,在悲愤之下,推到棉纺机后发现的。可如何让棉线不断头,就要靠精密的装置了。她病了之后,关于棉大纺车的探索就被搁置一旁,她哪有精力去召集工匠做这种事呢?
贞筠黛眉深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至少,她已经让市舶司的目光又一次聚到了棉布上,而不是只盯着上层的绫罗绸缎。
而还困在家中的谢丕,浑然不知贞筠去而复返。他正在焚香鼓琴。屋外秋雨萧瑟,屋内亦是一片凄清。他十指拂过琴弦,所奏之声慷慨激越。
待到曲终,礼叔才开口道:“一爷,再这样下去,咱们就要顶不住了,要不,还是走吧。”
谢丕没有回应,反而问他:“您听出我弹得是什么曲子吗?”
礼叔就是谢丕之叔谢迪的奶兄弟,在谢家耳濡目染,也通诗书,可如今他心乱如麻,哪里有心思听这。
谢丕也明白他的烦忧,他道:“这是《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连魏国先民都愤恨上层不劳而获、敲骨吸髓,何况如今呢?”
礼叔一愣,道:“可又不是咱们在这里侵夺民财,咱们在灾荒年间,还放粮救民呢。冤有头债有主,他们要恨也该找对人才是啊。”
谢丕道:“可要杀我们的,也不是平头百姓啊。”
礼叔道:“那些人就是憎恶我们,夺了他们的好处。一爷,我看差不多也就行了……闹大了对老爷的官位也不好啊。”
谢丕摇摇头:“事情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恰如宝剑出匣,必见血而归。”
他沉默片刻后道:“礼叔,既然挡不住,就别挡了。”
礼叔一愣,只见谢丕微微一笑:“保留实力,还能控制局面,要是真被逼上绝路,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谢云得知消息时,伪装成乱民之人已然闯进了谢家一房。当其他阴私手段都无济于事的时候,豪族也只能一力破万法。
谢云惊得魂飞天外,他道:“怎么会这样!来人,带上家伙,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他带着家丁气势汹汹地冲出去,可还没走出家门,就被他爹拦了回来。
谢述简直要被这个不知轻重的儿子气死:“站住,畜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谢云惊疑不定:“爹,一房被攻破了,堂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