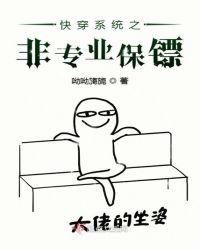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HP同人)摆渡人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那天晚上,西里斯一样给我讲过睡前故事。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整个人的态度,与往常不太一样。或者是因为我们两人同榻而眠的时候,我总是习惯性地伸手抱着他的腰。而他一般靠坐在床头,或者给我念书,或者抚着我的头,眼神看向很远方,对我讲那些近乎于匪夷所思的故事。可是那一天他与我一道躺卧,从背后牢牢扣住我的双臂环抱身前。讲的故事,也是在我耳边低回。虽然内容并无任何浪漫抒情,可是情态始终婉转缠绵。我也渐渐觉得,好像不知何处是故事,何处又成了我的梦境。他对我讲世纪之交的北欧。说那时候的挪威,港口上遍布精心设计的经典式建筑,漆成温和的粉彩颜色。烟雨中远远看过去,总觉得整座城都带着一重雾气蒙蒙的滤镜。又或者不如说,所有后世的滤镜,胶片的处理,全数是在仿造北欧的迷雾。那时候的挪威,足以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海岸线,承载着这世上最美的冬天。他说世纪之交的奥斯陆,有个男孩子出生在当地的城市医院。那时候的城市医院,已经演变成了一处妇产医院,在此地出生的孩子,大部分会被遗弃。好一些的会有人领养,运气差一些的流落到各处福利院当中,很多不能活过人生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不像是一般的新生儿一样浑身红粉,反而带着一种寒冷的苍白,白得能看见皮肤下蓝色的血管。像是因受寒而亡的人那样的颜色。助产士都以为这应该是死胎,但意外之中,这孩子竟然活了下来。他的生母无力对其进行抚养,可以想见大约是未婚生子。幸运的是,这孩子被旅居此地的一对英国夫妇收养,带去了距离苏格兰不远的约克郡谷地。他们两人在此处有一间乡村宅邸,群山环抱之中,漫山葱郁林木高低成片。此地雨水丰沛,天光从云层中倾洒下来,随着羊群四处游荡。那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虽然称不上多么富裕,但是至少衣食无忧,也受到家人的爱与关怀,是个非常善良温和的人。预备成年后,准备离家去约克或者利兹的某手艺人处做学徒,如此可谋生。又或者可以去附近大学念一门农业科学,如此可以继承家业,成为新一代的牧民。一九一四年三月十日,他满十八岁。同年七月二十八,一战爆发。他与其余同龄人一样,被强制征兵入伍,成为英军步兵的其中一员。一九一六年,被派往欧洲本土,法国北部,索姆河。他的样子,可以称得上是很文弱。皮肤始终是一种常年不见光的苍白,又因为读多了书,说话时的用词与口音,与其余士兵很不太一样。大约也是因为这些特质,从征兵第一天起,就始终与其余人格格不入。一旦真正开始行军,常常受到同僚的排挤。不与他说话谈天是常态,更糟糕的时候,曾经在他的睡袋中放过捉来的耗子。到了欧陆,每天步行行军的时候,会逼他打头阵。概因战场上大概率埋了地雷,德军撤离的时候,常会设下这样的陷阱。地雷与铁丝连接一起,遍布行军路线。打头阵的人,最大概率会踩到这样的铁线引发炸药,生命安全也就最无法保障。可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同僚进行报复。可是这样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大约不觉得是善良,反而觉得是软弱。如此对于他的排挤和欺凌更加变本加厉。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索姆河战役打响。这场不列颠军队,法兰西第三帝国与德军之间的对弈,从一六年七月,一直拖延到当年十一月十八日。足足一百四十天,共有三百余万人参战,其中阵亡将士一百多万,足称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在英军遭受重大创伤后,军队决策将北部战线的步兵也一并调往索姆河。年轻的约克郡士兵,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很快被席卷进战局之中,在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寒冬之中,牢牢镇守住河这一边的防线。冬季粮草短缺,连伦敦城都已经开始节衣缩食,民众购买食物只能使用粮票,遑论是远离英国本土的索姆河战场。无尽的雪野,灰暗的长冬,只能靠干面包或者土豆度日,有的时候这也没有,只能在附近的森林中寻找野草充饥。某一日轮到他当班,去寻找可食用的植物的时候,步行很远,但临近树林已经被毒气弹侵袭,几乎寸草不生,寻找甚久,只在雪下找到一小把枯死的蒲公英。这一把蒲公英,不足以填饱任何人的肚子,但也只能如此。他带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收获回到营地,果不其然受到其余人的嘲笑欺凌。说话之间,就有人将他压在地上,硬逼着要将那一把蒲公英塞进他嘴里。他只能咬紧牙关,预备只要有人成功掰开他的嘴,就要把对方的手指也咬下来。挣扎之中,泥泞满身,连眼睛也难以睁开。忽然间听见剧烈的咆哮声,而后觉得身上压着他的手一松。借机翻身而起,看见他的身前,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只巨大的黑犬。几乎可以说像是高加索獒犬一样的体型,正在对着那些欺凌他的同僚疯狂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