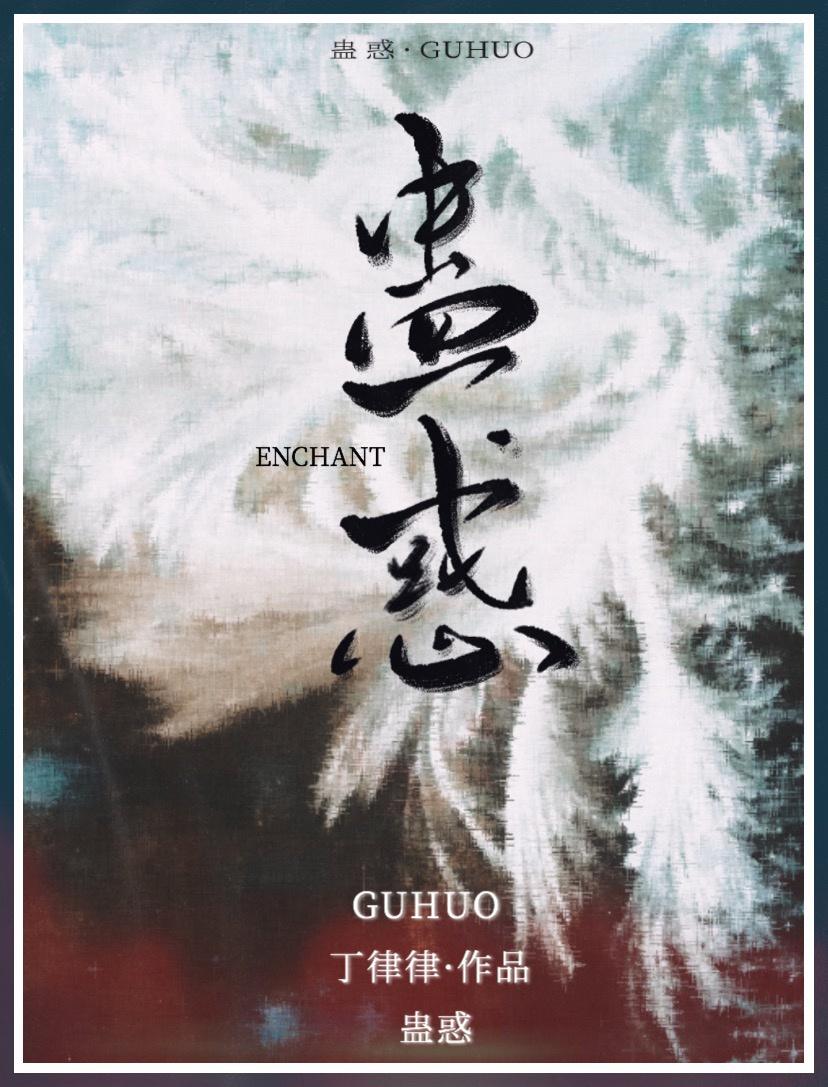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汉]家父汉武帝 > 4050(第49页)
4050(第49页)
刘据哼唧:“才没有呢。我刚做好,都没尝就拿来给父皇了。”
刘彻轻笑。
刘据递给他一根,转头好似才发现李姬的存在一般,眨眨眼:“李姬也在啊,李姬要吃吗?”
李姬已被他们的到来吓得神魂聚散,唯恐他们是来揭发鄂邑的,哪里敢应,下意识摇头:“不,不用了。”
刘据也不强求:“李姬可是来找父皇说二姐之事?”
不待李姬回答,转头又问刘彻:“父皇,听说张汤已查明事情原委,此事全是广仲恶念之下出手,并无旁的隐情。那二姐那边是不是可以解她禁足了?”
“你想帮她说话?”
刘据并不避讳,直接点头。
刘彻轻嗤:“确实没有隐情,但不代表她无辜。据儿,朕不信你既能发现采芹的异常,会看不出鄂邑言语之蹊跷。”
“我知道。但就算其中确有二姐手笔,广仲仍是首罪。因为二姐话语只是陈述。陈述醉马草的用途,陈述自己与王充耳的婚事,没有任何诱导之词。这点张汤审讯过广仲,也查证过当日在场之人,都可佐证。”
确实如此。刘彻并不否认,但也没有接刘据的话,静静看着他,不言不语,态度不明。
“所以不论二姐如何,广仲确实罪大恶极。”说到此,刘据面露嫌恶,“如今是他失败了,想尽办法脱身,因此不惜咬出二姐。但若他的谋划成功了呢?是不是现在已经高高兴兴让修成君来向父皇请求赐婚了?”
说完拉住刘彻的胳膊,义愤填膺:“父皇可知,广仲之前还肖想过三姐,同三姐献殷勤呢。”
刘据咬牙切齿,刘彻脸色也瞬间垮下来,看向诸邑:“他接近过你?”
诸邑点头:“是。”
刘彻蹙眉:“怎不见你提?”
诸邑轻笑:“不是什么大事,也配拿来让父皇烦心?女儿不理他便是了。他又不敢把女儿怎么样,何须在意。”
不在意跟有没有这回事是不一样的。刘彻神色冷沉。
刘据接着说:“何止广仲,王充耳也不遑多让。不说三姐,若不是知道长姐早与曹襄表哥有默契,王充耳怕是还想试一试长姐呢。一个两个全是癞蛤蟆,偏都想吃天鹅肉。长得挺丑,想得挺美。呵。”
刘彻看向诸邑卫长。
诸邑点头。卫长轻叹:“王家手握太后遗愿,但太后遗愿只有一次机会。自然要牢牢抓住,让利益最大化。”
如何才能让利益最大化?鄂邑生母身份低微就算了,还不受宠,哪里比得上皇后嫡出。
而皇后嫡出中又有高低之分。不管是封邑还是帝王宠爱,卫长都是独一份。若能娶到卫长,王家便可重临太后在世时风光最巅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王家虽然“心大”,却还没有失心疯,所以他只敢想一想,小心翼翼做一二试探,察觉到曹襄与平阳的举动,知道自己比不过,立刻退场。
即便如此,他们曾有过心思,也很让刘彻恼怒,脸色黑沉如水。他也是看不上王充耳的。但为了太后遗愿,他不介意舍弃鄂邑。可这不代表他愿意舍弃诸邑跟卫长。
王家,王充耳,简直好大的胆子!
不过他眼珠一转,收敛怒意,看向刘据,眉宇讥讽:“为鄂邑,你倒是有心了。”
刘据如何不知他此话的意思,立时挺直腰杆:“我承认我想帮二姐,但不论广仲还是王充耳,我所说绝对句句属实,绝无虚言。父皇不信可以去查。随便查。”
信誓旦旦,只差指天发誓了。
诸邑卫长也道:“不敢欺骗父皇,确实为真。”
刘彻轻嗤,他当然知道为真。不说这几个孩子敢不敢随意欺骗君父,只说这种谎言一戳就破,三人都不傻,怎会干如此蠢事。
但他们此前不在意没有提,如今来提,也确实是在借此为鄂邑说话。不过显然三人将心思直接摆在明面上,没想瞒他。
所以刘彻虽出言刺了一句,却并未恼怒生气。
他轻叹:“据儿,你可还记得疯马差点冲撞到你?”
“我记得。父皇,此事为意外,二姐并无害我之心。若我确实因此受损,我自然会怪她怒她,甚至对她出手,都不为过。
“但我安然无恙。这其中即便有二姐设局,局也不是针对我。如此,我仍旧怪她怒她,甚至对她出手,那么其他兄弟姐妹呢?”
其他兄弟姐妹?这跟其他兄弟姐妹有何关系?
刘彻愣住,卫长诸邑也有些懵。
刘据继续:“父皇正值壮年,我虽如今兄弟姐妹少,不代表日后会少。若我是这样的性子,睚眦必报,日后兄弟姐妹要如何与我相处?
“他们会不会战战兢兢,担心偶然做出某件事,本与我不相干,却因为我突然闯入,差点累及我,即便我无损伤,也会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