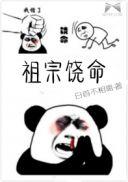墨澜小说>重新来过 >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第1页)
说完他猛地咳了几下,像是要把肺咳出来,特别凶。如果他是想引起我的同情心。他成功了。我不想去关心他得不得病,只是这个病人就在我眼前,他身体虚弱,眼睛湿润,脸上甚至泛着不正常的潮红,全身风尘仆仆,没有好好的打理。稍微有点同情心的人都做不到虐待病人的事,我伸手理了一下他的头发。他眼睛一下子亮起,里面充满惊喜。我忍住心酸,说:“我们到下面吃点算了。”他高兴地点点头,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别问我隔着口罩怎么看见的,我眼睛又没瞎,他的眼睛笑得已经眯得快看不见了。唉。我爱他或不爱他。他不去追求,我也不去想。如今很好,过得安定。在往楼下走的路上我假装无意间问起:“你的病好点了吗?上次好像病得都不能主动拿手机。”“快好了,我就是这样,体质不是特别好,加强运动也就这样,所以我爸才没给我丢军队,怕到时候病死。”……谁问你这个。“这样,那你别总是过来折腾,在家好好养病。”“噢,你刚刚说钟弥对吗?他给你打电话了?事后我知道骂了他,他那天是来看我的,我一直喊你名字他就自作主张拿我手机联系你,以后我不会让他碰手机了。”本来不行继续聊的话题再次被他带偏,我承认我是个自私的小人,是藏匿在洞里不见天日人人喊打的老鼠,心里龌蹉的想法不敢承认,我所有的不甘似乎埋在我的内心,谁都不知道,唯有我知道。行动彻底把我打败,它和我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存在,一个用于直面,一个什么也不敢面对。我想说我输在他什么地方,第二次――第二次的你不是都已经喜欢上我了吗?为什么一句解释都不屑于对我说。凭什么呀?他如此珍贵,所以我只配被践踏。我缓过神发觉自己又陷入这类情绪,垂着头平静地说:“该怎么样怎么样,别刻意。”他点点头:“我知道,我以后离他远点。但毕竟我俩家关系比较好,还是会有接触。”“随你。”我觉得没意思。我只是觉得没意思,也不用对人提。我小时候对爱情有些憧憬,见识太多后知晓人生不过是玩玩而已。纯洁的我却又不小动了真感情,被弄得遍体鳞伤,纠结于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最后像火烧了一样成了灰。我明知道他们在玩弄世人,却忍不住被吸引。也是活该。暮斯突然揽住我的肩,我吓了一跳,还没等我说什么,他把口罩拉到下巴突然俯身亲我的脸颊,又靠在我的肩上在耳边说话,低沉的声音传来。“走这么快干嘛,我都快追不上你了。”“我和他……和他真的没什么,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我无所谓地答道,“别靠这么近,别人看见就不好了。”解释是为了什么。我心里又叹了一口气,又是一件无意义的事,可人总喜欢做,因为觉得有意义。他黑着脸恼怒得用牙尖轻咬我的耳坠,恶狠狠地说:“盛朝。”如果说上一次是我的错觉,那此刻我真实体会到,暮斯的嘴唇很热,说话时喷出的气体也是热的,我的耳坠也在隐隐发烫。它应该红了。可惜我脑子糊不过三秒,我马上反应过来对方正处于感冒,怕他把感冒传染给我,而且他现在就像个易炸品一碰就炸,为了安全我决定离他远点。下定决心后我快走几步,到了他的下方,转身直视着对他说:“暮斯,这样很好,你知道的。”所以不要再去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我的意思他听懂了。他的脸色微沉,大约是气到不行,他把口罩重新戴好,手却在微微颤抖。他说:“好。”我把我的所有给他,他嫌不够,于是我捧上我的真心,他嫌弃廉价,等我顿悟离开,他又后悔。真累。谁爱做谁去做。我不去当那个傻子。我可能是真的不在意,但我得学会一遍一遍地警告自己,警告自己别再去撞南墙。112吃饭的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陷入安静。说是大家其实只有我们两个。我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喝着小酒。暮斯没有制止我喝酒,我觉得有些上头,酒好喝还让人沉迷,当我的酒见底,就喊上服务员再来一瓶。刚给倒上一杯,一只手伸到我面前。我暗叫一声惨。果然,他把杯子和酒拿到自己面前,挣扎都无力。随他吧,没有酒我吃不下多少,何况回来前我已经吃过,我搁下筷子等他吃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