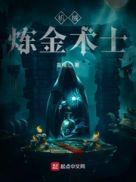墨澜小说>红僧衫 > 12孽主(第2页)
12孽主(第2页)
只见这院中催花折草的,独独几根直立的草叶都在滴血。闯进了新人,那爬跪于中央掏吃脊髓的妇人骤然抬头,满面都是肉渣血块。
谢临风和祂遥遥相照,摸到腰上:“这般雅致的亭廊,竟被你暴殄摧折成这幅样子,你化孽主而来,好恨是不是?”
话音未落,谢临风便挥鞭而上。孽主伸向人肚的手被骤然挨上一鞭,“滋滋”作响,似是又要烧起来!
孽主对方才他们二人烧祂傀影一事怀恨在心,当下发狂,匍匐爬行而来。谢临风拍飞肩上的荧鸓,率先迎战。
孽主化手为足,四脚发力,张开血盆大口朝谢临风扑开。秦夫人本就肉体凡胎,如何受得了这样扭曲,当即嘴角爆裂,下颌脱臼,悬在脸下。
谢临风挥鞭缠绕住祂的脖颈,挥舞将其打到一旁,喝道:“我这天下鞭远胜罗刹,你若听得懂,便趁早出来。三鞭过后,我定将你魂魄打散!”
孽主听罢,远远绕着谢临风爬行,知道谢临风不是假话,不仅是祂,但凡鬼怪,皆忌惮他的血罗刹三鞭。
祂向前爬了两下,似乎是个示弱的信号。谢临风凝滞片刻,并未收鞭,不料仅瞬息之间,他骤然抬臂一挡,喝道:“你很好!”
这畜生果然天不怕地不怕,偏要和他拼命!
孽主咬住谢临风臂膀,又被甩了出去。祂“嘭”地撞上墙壁,跌落伏地,顿时发出桀桀笑声。
谢临风鞭红如火:“你笑什么?”
他刚说到“么”字,那孽主摇摇晃晃起身,嘴里嗡嗡作响,像是在念着什么咒语,这音调注入谢临风耳中,陡生出一股熟悉感。
谢临风正费解着,电光石火间,他周遭忽然显出几个黑黢黢的窟窿洞,它们咕噜咕噜冒着泡,正一边沸腾着,一边朝谢临风拢聚起来。
谢临风道:“你要再召傀影,是要同我好玩?那我便叫你好看!”
他正要跃身,忽觉脚下一沉,那洞里瞬间爬出几只手来,要将他拉下深潭。奇了,这里的手竟和刚才抓菩萨的手不大一样,它们臂腕上画着修狃族的图腾,每一处力道都是禁锢的咒语。
谢临风看到图腾,却想到别的:“傩祭吟唱,我知你是谁了。巫人一族,你是白芍!”
正在此时,晏病睢飞身跃来,朝手臂挥剑砍下,那长剑骤然断成两截。他道:“下咒了?”
谢临风笑说:“既是共患难,迟些也无妨。晏兄,我们正等着你呢!”
眼看那黑洞已吞了谢临风半条腿,这家伙大难临头,还能说出孟浪话。晏病睢冷哼一声,用断剑朝孽主刺去。
与此同时,孽主忽然抬起手臂,祂手中空空,却像捏着柄扇子似的,轻轻晃了晃。
谢临风见势扬鞭,将晏病睢裹了回来,环着人:“祂正等你呢!”
晏病睢两头迷惑:“等我?”
一阵狂野风浪冲撞而来,不仅掀翻了晏病睢的幕离,还险些将人刮走。谢临风一手捂面,一手圈住菩萨的腰。几次下来,谢临风早知道晏病睢脸酸心硬,独独这弱柳腰是软肋,逗不得。
“你跟个风筝似的,我碰一下便碰了,这叫下策!”谢临风箍着怀里的纸片,迎风道,“你再摆脱一下,我可就真撒手了!”
晏病睢怒道:“你撒。”
“我撒什么,明明是你在撒气。”谢临风觉得很有意思,新奇道,“身份不是我透露的,帘子不是我吹飞的,我救你一回两回,你就独独记恨我?”
晏病睢不语。
风停,谢临风捂着胸口将人放开,像是心里在痛似的。他强撑着桌子,破罐子破摔:“恨我,那恨我吧!”
晏病睢道:“等会儿再恨。”
“又等会儿再恨了?”谢临风称心如意地抬头,眼前蓦然映入几盏红烛,那火光似是有力道般被灌入识海,让他神色微滞,“我们又回来了?怎么同之前差别如此之大!”
二人正是进入了当日的魇境石窟,只是眼前这石窟有很大不同,这其中做了布局,种了火树琪花。
金窗玉槛,红绸幔帐,“囍”字高挂。
各处角落,皆是红烛摇曳。
谢临风猛然缩回手,他道:“好险,好险,差点糟蹋坏了。”
原来他方才撑在桌上好一会儿,压的并非桌布,正是两套堆叠整齐的婚服,上头金丝线刺绣精致,谢临风正端详着,忽觉身旁之人僵了下。
谢临风道:“晏兄……”
他喊到一半,便呆了。
晏病睢说:“……嗯。”
谢临风道:“你……你怎么有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