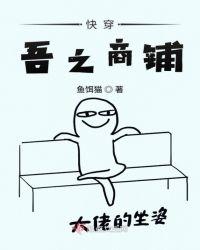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却拂华 > 第 10 章(第1页)
第 10 章(第1页)
饭桌上,宋鸷章旧事重提:“现在咱们一家子终于团聚了,前几天我已经安排过了,明日就可以带你们入宫。”
听到入宫易槐西没有半点反应,而易殊却眉头紧蹙,拒绝道:“谢谢您费心安排,我和娘还是打算在这里生活。”
说完,他看向易槐西,想确认她是不是和自己想法一致。
易槐西点头看他,表示赞许。
而宋鸷章却拉下脸来,声音也沉下来:“胡闹,哪有皇帝的妻子儿子待在宫外的?”
易槐西夹了筷排骨放到易殊碗中,面无表情地回他:“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是这么过的,殊儿不愿意的话,那便继续在这里生活就好。”
她看向宋鸷章,眼里没有一丝温度:“你要是愿意可以每天多来看看殊儿,至于你我,早已无任何干系。”
宋鸷章将筷子啪地摔在桌上,恼她当着孩子的面儿说这些,看着她却说不出责骂的话:“其他什么都可以随你,唯独你们想留在宫外,这不行。”
易殊正欲反驳,却被易槐西拉住手,“不行便不行罢,总归如今你是天子,我等皆是臣民,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吧。”
易殊一脸郁闷地看着她,她却摇摇头不愿多言。
宋鸷章见她半推半就,便也借坡下驴,吩咐一旁的刘启盛着手安排,明天便带他们进宫。
月明星稀,皎洁月光洒在庭院中,杏树叶儿悄悄舒展开,马儿和阿黄也在月光下沉睡。
宋鸷章走后,易殊来到易槐西屋前,正欲敲门,门却从里打开。
“进来吧。”说完她转身进屋,易殊紧随其后迈入里屋。
“娘,我们明天真要进宫吗?”
“怎么?殊儿不愿意吗?”易槐西端着茶碗吃着茶,故意似的回他。
“我也不知道。”易殊抚上茶盏,淡淡抒发自己的心意:“小时候我总希望我也能有父亲,希望你能少些辛劳。”
“现如今真有这么个人出现了,我真。。。。。。不知如何与他相处。”
易槐西看着易殊耷拉着脸,狡黠道:“你随他进宫的话,总归荣华富贵是不愁的。况且如今他膝下仅有一子,你就不想去争一争?”
易殊抬起眼看她,恼她这时候还逗趣:“我是觉得如今这日子正是我想要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虽忙些,但也充实。”
“听了您给我讲的那些事儿,对于那些权谋算计,我更是只想远离,丁点儿不想靠近。”
看着易殊这般,易槐西默默叹了口气。她也无比憧憬简单自在的日子,可惜往往天不遂人愿。
目送易殊离去,易槐西彻夜未眠。
天初破晓,易槐西推开窗,长吁一口气。初晨的空气清冽,她感觉浑身都似脱胎换骨般,身体也不似往日沉重。
她到院中看了一眼染上晨露的石桌、将败未败的栀子花、还有渐绿的杏树,马儿将醒未醒,半合着眼。
阿黄向来是个贪睡的,现在还在它的小窝里呼哧呼哧呢。察觉到熟悉的气味,阿黄恋恋不舍的离开狗窝,惺忪着睡眼要她摸摸头。
易槐西看着这只陪伴自己不足两个月的小狗,比之先前已经长高了,也长大了。她温柔地抚摸着它的脑袋,抱起它,感受着它扑通扑通的心跳。
她狠狠心,放下它,让它回狗窝里继续睡。狗狗被主人温柔爱抚后,心满意足地蜷起身子,继续沉入梦乡。。。。。。
易槐西转身回到屋里,从层层被褥下翻出早已准备好的东西。
分别是一瓶见血封喉的毒药,还有一把匕首和一封绝笔,她将信放置在一旁。
她拔出匕首,那雪亮银光刺目,她将毒药抹在匕首上,上榻躺好。腕间传来阵阵疼痛,感受着血液渐渐从她身体里流逝,易槐西的心脏麻痹,慢慢的血管封闭、血液凝固了。。。。。。
这一世太苦,若有来世,愿她只作那翱翔天际的鹰、驰骋原野的马、游走林间的蛇。。。。。。
易殊昨夜将近寅时才入睡,他起时,院中已有成群人在候着。有一袭黑金制服的禁卫、有身着桃红宫装的宫女、也有一身绛紫色长袍的公公。
刘启盛见易殊出来,忙不迭地迎上去:“大皇子您可算醒了,早膳已经备好了,您和娘娘用过后一道随奴才进宫吧。”
易殊对这些场面说不出的抗拒,也不适应这些称谓。张看四周未见到易槐西,他便往她卧房行去。
他敲门不应,便喊道:“娘——”
屋内却迟迟没有人应答。
他推开门,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他脑子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牵扯着,犹疑地往那浸血的床榻上看去。他走向前,手微微颤抖,凑到易槐西鼻尖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