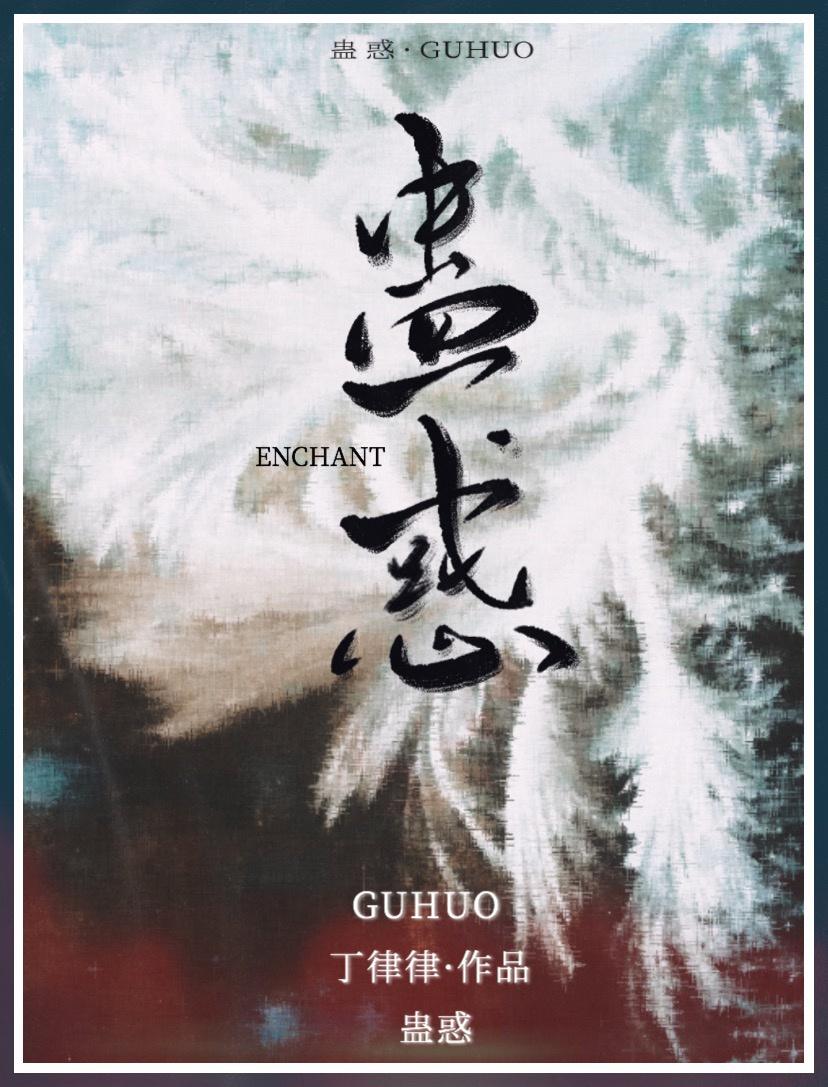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穿成纨绔后直接躺平(穿书) > 第42章(第2页)
第42章(第2页)
我没记错的话,一开始确实有人见我不习惯国子学的生活,热忱的帮我送了几天饭食,那些不是我在外头结交的狐朋狗友吗?没你们的份儿吧?这功劳你们也想强占?不应该啊!再说打从他们影响我读书被司业抓住,扭送到祭酒处后,便改过自新再没来打扰过我上进读书了。
后来我都是和十三殿下一道儿同吃同住,同进同出,你到底都关怀了我什么,我怎的半分都想不起?具体说说!嗯?”
那人脸憋的青紫,他们这些人往常极力讨好荣舒朗,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在他跟前留下一丝半点的印象,好从荣府,从荣伯府手里拿点好处吗?本以为这是双方心知肚明的事情,结果现在这人一脸无辜的跟他说,他从未体会到他们的讨好卖乖,那他们往日种种又算作什么?
笑话吗?
好吧,如今荣伯府深陷泥沼,荣府独木难撑,荣舒朗失势也是迟早的事,往日的讨好注定要打水漂,他们也早就成了旁人眼里的笑话。为了挽回几分颜面,也算出一口心中恶气,他们势必不会让荣舒朗好过!
可他竟轻飘飘一句“想不起”就想打发他们,休想!这人顾不得失仪,直接起身,疾言厉色道:
“说你忘恩负义卑劣小人你还不认!今日在场二十三人,哪个没有帮你去饭堂拎过食盒?哪个没有帮你洗过衣裳?哪个没有为你在夫子跟前说过好话?国子学众生亲眼所见,你都能抵赖,我此生从未见过你这等厚颜无耻之人!”
舒朗松开攥住对方衣衫的手,嫌弃的甩甩,十三皇子适时地递上一块儿帕子:
“擦擦。”
舒朗边擦手边漫不经心道:
“我也从未见过你等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啊,你们不主动上门,我都懒得和你们计较,既然你今儿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那咱们可得好好说道说道。
先说帮我拎食盒打饭之事吧,因十三殿下身份尊贵,我又受太子嘱托,与殿下同吃同住,安全起见,外人送来的吃食是从不入我二人口。每餐饭我们都得亲自去饭堂盯着人盛饭,直到入口,期间绝不假手于人。
因此路上拦路主动要帮忙的,我们只拒绝了好意,没将之视为意图不轨之暴徒已经是看在同窗一场的份儿上。跟那些人周旋,除了耽搁我们吃饭时间外一无是处。
至于问都不问便将食盒送到寝舍之人,呵,只叫人将你们的食盒远远的扔了,警告你们别做吃力不讨好之举,那都是出于保护你们的善心发作!若不然十三殿下真用了你们送来的东西出了事,有几个脑袋够砍的?嗯?可长点儿脑子吧!”
要不是顾及十三皇子的安危,舒朗有段时间真的很想把以前那群狐朋狗友弄身边来继续薅羊毛,毕竟对方是真知道他口味,拿出来的东西他是真受用。
那几位拥有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极其丰富的拍马屁经验和手段,不管做什么都能做到舒朗心坎儿上。若不是对方早早转变了对付舒朗的思路,改了行事手段,舒朗都舍不得轻易和对方说分离。
眼下这群人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
舒朗无趣的摆摆手:
“再说说帮我洗衣裳这事,我请你们洗了吗?知道我衣裳好端端摆在床头,吃个饭的功夫回来就不见了,以为寝舍进贼是什么感受吗?知道我一件顶级的杭绸加上羽衣阁巧手绣娘亲手缝制,袖口以头发丝细的金线滚边儿的里衣价值几何吗?
那是要手上细嫩无茧的姑娘们用微微温热的水轻轻揉搓,放在熏炉下烘干的!你们倒好,用棒槌给我敲打成咸菜干儿,我还没找你们赔钱呢,哪来的脸跟我提这个?”
说起这些闹心事儿,舒朗悲愤交加,那会儿他自个儿都不晓得他穿的衣服如此讲究,祖母只说他“不爱洗衣也无碍,待休沐日全部带回家让下人清洗。”
当时他只反感这些人不经他同意就擅动他私人物件,直到后来回家被梨满抱怨了几句,才晓得他身上竟穿着一座京郊别苑。
别提多心疼了。
他这人给重视之人花钱,好比给母亲柳氏准备嫁妆,那真是毫不手软,能羡煞旁人。可外人随意拿他一个铜板儿,他都觉得窒息。
越想越来气,被舒朗视线狠狠扫过之人,十有七八心虚的别开眼,一两个自认没参与这些,还帮舒朗在夫子们跟前求情之人理直气壮的与他对视。
眼神里写满了“看你还如何狡辩”的高傲。
舒朗轻嗤一声,隔空指指几人:
“还有你们几位,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原本我犯的错,搁在别人身上最多罚站一堂课,或抄两遍文章了事。结果在你们的坚持求情下,我成功罚站一天,抄写翻倍!
一回两回也就算了,我当你们无心之失,回回如此,说你们不是故意的,门口看门的大黄都不信!是不是觉得自个儿特能耐,特仗义,我还得给你们敲锣打鼓送个仗义执言的牌匾?”
舒朗甩袖。
“龌龊无耻!斯文扫地!”
这种事太多了,舒朗以前懒得计较,权当调剂生活,这些人坑他一回,他便回坑回去,乐此不疲,若不然这国子学生涯也太过枯燥了些。可这些人千不该万不该,私下里舞一舞也就算了,今日竟还舞到他面前来耀武扬威。
舒朗隔着手十三皇子的手帕,拍拍领头那人的脸,不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