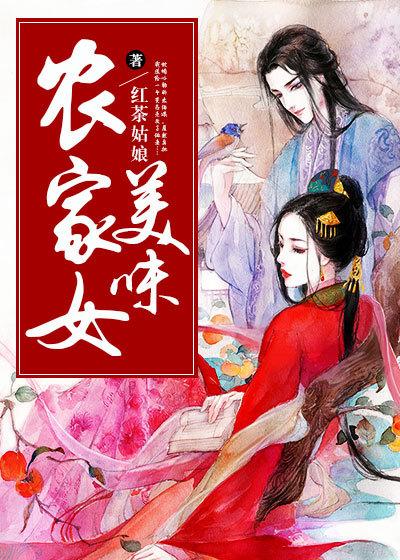墨澜小说>农门悍妻种田忙路小早 > 第180章 究竟害的是谁(第2页)
第180章 究竟害的是谁(第2页)
楚临渊嘟嘴撞了下容桓。
容桓没理他,“王爷,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请尽管吩咐,容桓甚至愿意代替临渊进京。”
“瞎说什么?”楚临渊白了他一眼,“怎么和三弟说一样的话?”
三弟是他庶弟他都不同意,更不用说从小一起长大的容桓了。
恭亲王见他这般,摇了摇头,“用不着谁代谁,渊儿隐藏多年,一直以体弱多病示人,却也不是为了今朝随便找个人代替他的;况且,这次还不一定得去京城。”
“什么意思?”楚临渊好奇道。
“咱们只需要盯着逍遥侯便是了,看他何时出发,他不动,咱们也不动。”恭亲王抿了口茶,“也不是个傻子,送上门去叫人拿捏了,毕竟当今皇上连父子亲情都不顾,更不是个怜惜手足之情的。”
他提及此事,容桓似乎心有所感,垂在身侧的手攥成了拳头。
王妃细致,关心地问道:“桓儿上次出去可有你弟弟妹妹的蛛丝马迹?”
容桓在他们面前不怎么掩饰,有些失落的摇摇头,“没有。”
“无事,不要多想,吉人自有天相;再或者,是你柳师父猜错了。”
没再说几句话,他们便离开了。
容桓转道去了他师父的院子。
他师父叫柳生绵,名字听着像个女子,但确确实实是个经天纬地的男儿。
从容家家破人亡后,除了最开始的一年,柳师父将他交给江姑姑照顾,之后的两年便是柳师父带着他东躲西藏,辗转来了梧州,一点点将他养大,传授他知识武艺。
十几年前,容桓的爷爷是前太子太傅,前太子楚天睿是先皇后的所生,他不像今上一样喜怒无常,不像今上一样疑心甚重,相反,前太子十分儒雅随和,亲贤臣、远小人。
楚天睿经常以太子之尊微服至民间体察民情,爱民如子,一度令百姓前朝交口称赞。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好储君,却在大熙六十年被人陷害,冠以谋反之罪。
皇上早已对他颇为忌惮,受人挑拨后,他竟丝毫不顾父子之情,突然赐了被幽禁的太子一杯毒酒,对外却说是太子畏罪自尽。
因此事牵连,身为太子太傅的容家首当其冲,全家被抄家灭门。
若不是柳师父的出现,容桓可能当时也会死了。
只是,他那时已是认字的年纪,所有事情不仅没有随时间的推移而忘记,反而越发在他的脑海中深刻起来。
他出神的想着,却发现自己已然到了师父的院门口。
里头有个人长身玉立,站在墙边不知在看些什么。他双手负在背后,脊背不是特别的直挺,却丝毫不缺风华。
原因无他,那一头披散而下的银发只用一根木簪挽起,如飞雪落瀑,又如流星飒沓,好像不属于这尘世,即将羽化。
“师父。”容桓开口唤他。
柳生绵转过身来,实际上他的年岁和恭亲王差不多,却不知怎么一头华发。
容桓也记不清了,好像从师父把他救出来,放在江姑姑那时,师父还是一头黑发的,第二年来接他时,就变成了现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