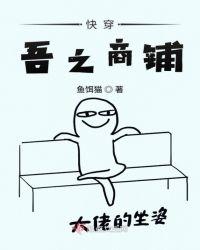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金爵钗 > 第五百一十九章 极目黑白十七(第2页)
第五百一十九章 极目黑白十七(第2页)
老道为女童仔细看过,也同此前大夫一样,说是受惊离魂之症。又问夫人:“去年可是发生了什么事,竟将她吓成这样?”
夫人犹豫了一下,如实说了:“我女儿自小有个仆人,同吃同睡,亲如手足。去岁家中长辈赐下一物,价值堪比万金,却在当夜失窃。长辈震怒,我只得叫人严刑拷打下人,原打算做个样子,不想那仆人却跑了。我女儿丢了自小一起长大的玩伴,长辈又打死了剩下的人,自那之后便如此,难吃难睡,如失了魂一样至今…”
夫人说到最后,掩面涕泣。
老道医术了得,又会些异术,便说治好不难。
夫人听后欣喜不已,却又听老道说:“既然是心病,自得心药来医。”
几根银针、两帖药下去,女童已安然入睡。夫人同老道一起守到夜里,女童醒了,眼神恢复以往清明,张嘴便说又饿又渴,抱着母亲的腰撒娇要吃要喝。
夫人赶紧命下人将温水药膳送上来,亲自喂她进食。
待她吃饱喝足,抱着肚皮仰面躺在床上,慢慢又睡过去。
夫人确信女儿已大好了,就要跪老道。老道却搀起她来,直道不敢当:“夫人与小姐命格贵重,哪里是老朽担当得起的。只是老朽观夫人病症似乎更加棘手些,还是养己身为先,日后万不可再惊再怒了。”
夫人点头说好:“只要
我的女儿从此无恙,哪怕天塌了我也不怕的。”
老道见又行一善,别过夫人后便离开了山院。
老道走后,夫人见女儿日日能吃能睡,似乎又回到从前。只是去年那件事,再也没听她提起过。
夫人总觉得有些不安。
重阳时节,夫人为女儿编花穗,恰好编了九条穗子,女儿十分喜欢。夫人试探性地问:“乖扶,你最近怎么不找阿九了?”
“阿九?”女儿睁着黑漆漆的大眼,迷茫困顿地问,“阿九是谁呀?”
夫人此时终于明白,原来心病需心药医是这个意思。
而真正的心药彼时早已登科,凭着檀家财力与能屈能伸的性子在翰林院如鱼得水。渐渐大家都知道,有个姓檀的修撰小吏,年少通达,相貌俊朗,不仅家境殷实,人也踏实勤奋,上峰同僚都很喜欢他。他乐助人,爱交友,脾气好到有人最后指着他鼻子骂他是铜臭商贾也不生气,笑吟吟地让别人多骂几句,他爱听。除了这点比较奇怪,平日里竟挑不出一丝错来。
他再也不是阿九,他是檀沐庭,集温良恭让酒色财气于一身的檀沐庭。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谁能猜得到他只是一个来自遥远的白龙珠城开贝人,做过光献郡主的奴婢,手上还沾有两条血命呢?
无人能猜到。
毕竟如果能猜到,不止整个翰林院,怕是天下都要大乱了。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诸如此类事,那样多消失的、死去的
人,总有那么一个两个若干个并不是意外或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