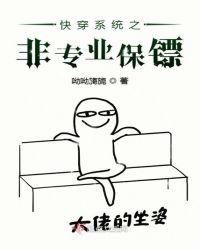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小王爷每天都在装风流 > 第237章(第2页)
第237章(第2页)
“好了。”沧渊微笑道,“叶知夏说皇上习武很勤奋,我还很高兴的。如今你与过去已大为不同了,不要想那么多,安心努力,好吗?”
许世景烁看到他脸上的笑容,内心里觉得有点恍惚。
他从龙椅那边走下来,来到沧渊身旁,拖了个凳子,说:“先生坐。”
沧渊温和道:“皇上没坐,臣怎么能坐下?”
许世景烁撩起龙袍坐在了地上。
他把沧渊拉坐下了,从低处仰望他,就好像自己还年幼时一样,这样看着他的先生。
“朕错了。”许世景烁为了最近的怀疑道歉,“先生是为朕返京的,又因助我一臂之力,而得罪了国公,才不能回家。朕不该听信他们的话,疏远先生。”
“我并未觉得疏远。”沧渊叹息道,“皇上忧心战事、关心政事,就是我所愿。”
“是啊……乌藏是乌藏,鞑靼是鞑靼,无论先生和可汗是不是好友。”许世景烁碰了碰沧渊的手,他能做的最多也就如此了,似乎怕对方厌烦似的,都不敢像过去一样直接握住。
沧渊这回却没摸他的头,而是道:“再过两年皇上就及冠了,是一个大人了。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太监看了都会笑话。”
“有时候想做个小孩,先生还会教朕,待朕亲近。”许世景烁看着沧渊粗糙带茧的手,“有时候又想赶紧长大,可以护住先生。”
他幼稚地怨天尤人道:“这样不大不小的太烦扰了,生活总是不如意的吗?”
“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沧渊垂眸,忽然问道,“礼部递上来的选秀折子,皇上为什么又给打回去了。”
许世景烁滴水不漏地道:“北境不安,便是业未立,朕怎可成家?若是批了,折子又会落到国公手里,他许久前就想为朕张罗婚事了。”
他说着说着便鬼使神差地问道:“先生想要朕纳秀女,立中宫吗?”
沧渊像个慈父一样,既是提醒,也是劝告般说道:“砍了树,以免乌鸦聒噪。”
“什么?”许世景烁没听懂。
“纳便纳吧,皇上不是嫌他们烦吗?把这事了了,也省得众臣总是念叨。”
沧渊说得很好笑,把“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大臣们比作聒噪的乌鸦,就是想逗小皇帝乐一下。
许世景烁却没有笑,眼神逐渐变得灰败:“知道了,原来先生是这样想的。”
……
夏末,兴京还很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