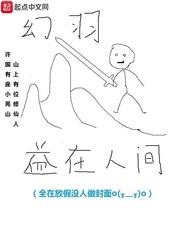墨澜小说>暴君宠婢 > 第89章(第2页)
第89章(第2页)
靳川言自荐枕席失败。
他知手链打好之后,便做足了准备,故意不束冠,是为了方便,穿着衣襟宽大的袍袖,除了方便外,也是为了引诱,可?惜了,他使?出浑身?解数抛出去的魅眼,都抛了个空。
时尘安这?个木头,纵然也饱览春宫图——一本——却仍旧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
纵然狐狸成?精,也没有办法让一个天残动春心不是。
但靳川言并不气馁。
他道:“过来。”同时,又把手腕上扣着的那沉重链条拖了起来,才这?么?会?儿,套环已经在他腕骨上印出了红痕,他却仿佛不知痛似的,若无其事地向着时尘安笑。无限好文,尽在52shuku
时尘安却不能不把这?点伤当回事,她知道链条很重,靳川言单手举着免不了酸痛,因此快步走到床边,才刚坐下,她的身?体便被靳川言顺势一拉,摔倒在他的怀里。
靳川言的手与冰冷的链条一道贴着时尘安的肌肤,他扶着她的脸道:“我现在失了自由,你可?以对我做任何的事,知道吗?”
时尘安仍旧懵懂,可?已经隐隐能察觉到了几?分?危险的气息。从前?她与靳川言不是没有靠得如此近过,他也不是头回扶着她的脸颊,可?是过往的每一次,都没有一次如这?一次被,让时尘安有一种被狩猎者盯上的感觉。
她清清楚楚地从靳川言的眼里看到了浑浊的欲望。
本能叫时尘安赶紧虎口脱险,但仍旧迟了一步,狩猎者总比猎物有更为敏捷果断的行动,在她念头刚起时,靳川言便一眼看穿她的念头,于是迅速地咬了上来。
或许不该称之为咬,而当是含,或者是吮。时尘安的脑内炸成?了烟花,无数的声音都在尖叫,可?是没有一道声音能告诉她当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唇上的触觉是从所未有的陌生,她才刚若脆弱的蝴蝶被人小心翼翼地捧起蝶翅,下一刻,就如顽固的河蚌被尖刀撬开蚌壳,被迫露出柔软无助的蚌肉,被裹着含口允与品尝,被迫吞下交换的津水。
时尘安一无所知地呆呆着任眼前?的一切发?生,也不知过了多久,靳川言轻拍她的脸颊,时尘安迟缓地转过瞳孔看向他,靳川言叹气:“时尘安,你笨死?了,怎么?连换气都不会?,竟然硬生生把自个儿憋晕。”
“我晕了吗?”时尘安有点呆,她回想了一下,并没有什么?记忆能佐证她确实有过短暂的晕厥,她只记得靳川言明明在舔她,下一秒,却变成?了拍她的脸颊。
那她大概是晕过了吧,时尘安并不确定,她问道:“刚才在做什么??”
“接吻。”靳川言看了她一眼,“你不是看了春宫图?里面没有?”
时尘安道:“春宫图没画这?个。”她想起了春宫图里画的那些,原本一知半解的画不知怎么?的,在当下的情境下,突然叫她生了些燥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