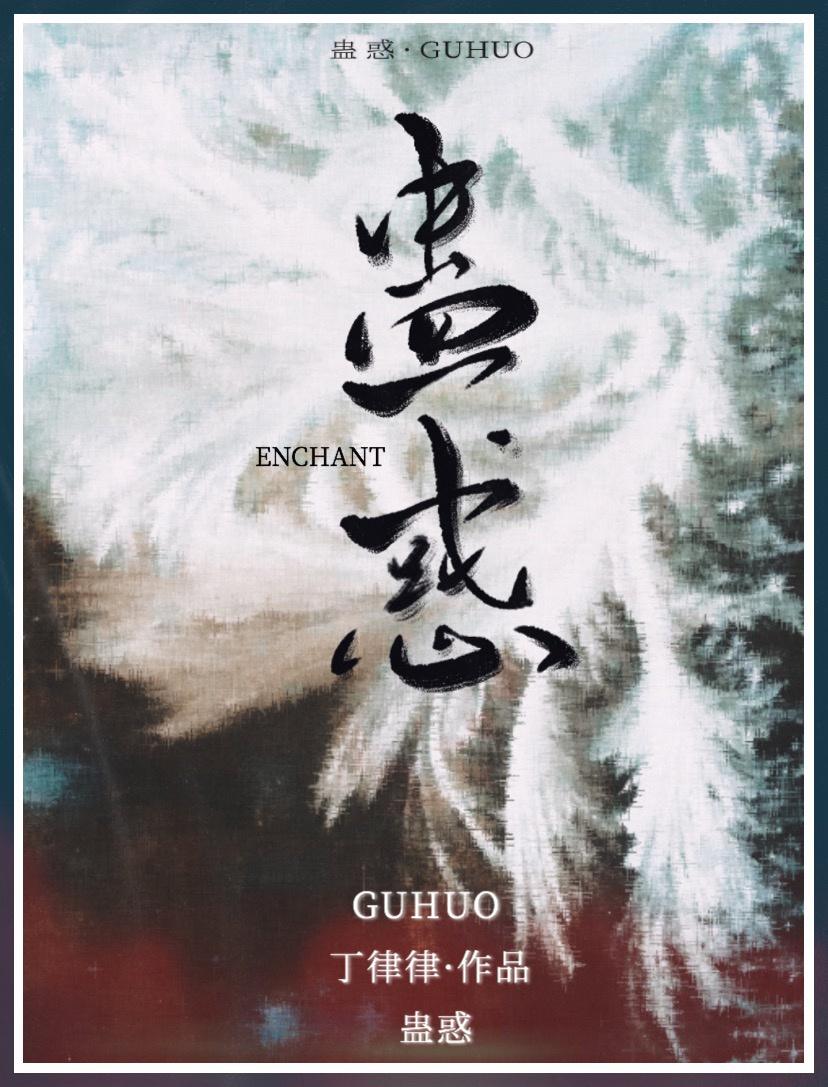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妄春 > 87白玉观音(第1页)
87白玉观音(第1页)
白玉之上,金线摩挲。他孑然一身的虚薄,亘古,覆灭消亡。他仰了仰息。太淡。浓水之下的淡泊。艳皮之下,被绳索束缚。他安静坐在椅上,从缝隙间朝我投眸。绿门斑驳,铁锁铐住,门面横杠,青光透入。他坐着,却如同死去。我愣怔扶上门,绿山石粉碎成齑。“和我说句话,萧欠。”我抖声着。他望向我,那双眼里却什么都没有。一切空无。“萧欠。”“和我说句话。”……没有回声。他沉入大片黑里。万千年的黑里。周身被黑遮得干净。他忽然伸手,在绳索间抽搐。动荡,木椅折碎,皮肉被绳索勒紧,他侧身倒在地上,长臂张出,啃咬在手腕。没有疼,面色太平常。直到手腕出血,血从口角滑落,渗入黑里,他吞咽下去,又用手指夹入嗓眼干呕。呕出水,后来什么也呕不出。青黄的水,混着血,大片腥冲着大片泔。我的鼻腔滴血,透在白上。我们浑身是血。我跪在地上,齑粉膈住我的骨络。我看着他,一如他看着我。失血的脸是苍白的,眼眶却是浓黑的。如尸体,似鬼影。泼天的大雨。那道门,隔在生死一线之间。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活着。溃散。成败。他的手腕淌血,却用指甲临摹伤口。血从夹缝间溢出,我看清他腕间的新旧疤痕。褐的是刀伤,红的是咬伤。他明明不会留伤,却遍体鳞伤。那是层迭而上的,未见好而被强硬剥开的。在痛与欲间的极致,他肆无忌惮地凌迟这幅躯体。那种疯狂磅礴,他从来为所欲为。滥用美色,又无所顾忌剥开自己的皮。撕扯,啃咬,他纵容自己的欲望。自虐的欲望,自杀的欲望,自我寂灭的欲望。哪怕被人束缚至此,却仍野蛮至极。他尝过血,空洞洞的眼里滚下泪。他的身体比他知道疼,他只是用沾血的手指擦去。眼尾太红,疼的红,血的红。我盯着他的眼,他回视我。静默中,我们纠缠不清,却又暗自博弈。青之下,一切皆亡。他疯得像要拉我一同死去。枕着满血的手,将身体与木椅扭曲。像是失去言语。“为什么自残。”我终于开口。门内古怪的声响,他抓不住自己的嗓。张口,没有生气,只有嘶哑的回荡。喉咙中,那息肉许久未用,又被手指捅伤。死寂之后,他涩声:“因为我想。”“为什么被绑。”“怕我死了。”“谁绑你的。”“朱志。”“为什么要找死。”他沉下去。等了很久——“因为我想。”“那为什么不直接处理自己。”他顿了顿。“因为我不想。”我躺在雨里,身下是碎了的山石。那本来是礼品。“你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他扬了扬手:“是。”“你没有痛苦过吗。”“有。”“痛苦什么。”“你。”“为什么。”“不知道。”“还痛苦吗。”“不痛苦了。”“为什么。”“不知道。”“你还爱我吗。”“不知道。”“你还恨我吗。”“不知道。”山石将我的白袍割破。我的骨头在疼。蜡黄的身体,死人的颜色。“我还能影响你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