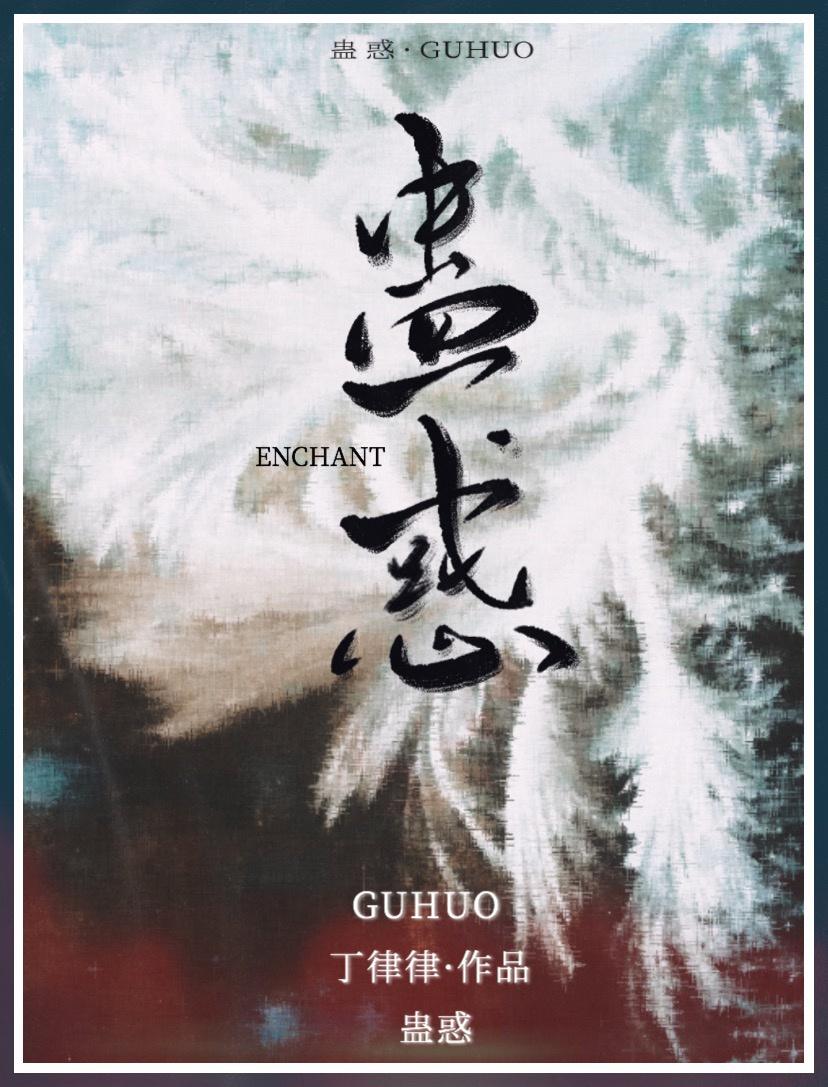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深情眼 > 第四十九章(第1页)
第四十九章(第1页)
叶鞲梁运安匆匆见过一面,王兴生的案子线索断了,一直没进展。市局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他们局长现在是顶着壁垒重重的五指大山,因为舆论压力不断,上头三令五申,不断下达破案期限。他们今年奖金可能需要倒找了,这案子还是像一团乱麻,毫无头绪。连先前的线索也都断了。
他们局长还是把压力抗住了。放话但凡这案子有任何疑点都不能匆匆结案。
“对了,”梁运安说,“我们聊下你妈妈那个案子,我始终觉得这两个案子直接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你妈妈的车是在九门岭的崖底发现的,对吧?”
叶鞯阃,“是。我妈是嫁到宁绥,她偶尔会到北京古玩城帮人鉴定古董。”
“那次也是帮人鉴定古董?”
“是,那是我恰好在北京读书,我妈顺道过来看我。她来时情绪就很不对,但她有抑郁症,我当时没多想,因为平时她隔三岔五就会发一次病,我当时看着她吃完药就让她赶紧回酒店休息。”
“之后呢?”
“之后警察就找到我,说我妈自杀了。”
“你妈那几天去过古玩城?”
“嗯,怎么了?”
“哪个古玩城?”
“镇南古玩城。我不太清楚,我只听我妈提过一嘴。”
“你没记错?”
“嗯。”
梁运安沉思片刻,随即问:“王兴生是镇南古玩城的常客,会不会那次就是他找你妈去鉴定?”
叶饕∫⊥,她没听妈妈提过。无从得知。
-
这一日,表婶又莽然找上门来。一点好脸色不给,大声责问李靳屿:“你那个老婆呢!”
李靳屿刚打开门,兜头被呛了一句,不太耐烦:“什么事?”
表婶气急败坏,一屎盆子不由分说地扣下来,“我们家高义从北京回来了,但是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肯开门!你那个女的到底对我们家高义做了什么!”
表婶说完,就地撒泼,一屁股墩儿死乞白赖地坐在地上,不肯走,也不肯让李靳屿关门。
李靳屿打电话给杨高义让他把他妈领回去。杨高义还挺听话,放下电话就跑过来,看见眼前这胡搅蛮缠的一幕,也是无语得很:“妈,你又发什么疯!”
表婶不管不顾,两腿一蹬抵着李靳屿的门框,无赖道:“妈还不是给你逼的!妈以为你在北京被人欺负了!这不是找你哥要个说法!”
人群密集的筒子楼,哪家嗓门大点都有人立马会趴着窗观望。别说这闹得惊天动地,李靳屿家门口已经围了一层厚厚的人在探头探脑地瞧好戏。李靳屿是挺冷淡的。但杨高义比李靳屿小四五岁,正是好面子的年纪,觉得丢人现眼,想把她拽走,可表婶就像一头蛮牛怎么拽都纹丝不动。
杨高义气急,索性撒开了闹。把人往地上一推,暴跳如雷将所有火泼了回去:“没人欺负我!我今天这样还不都是因为你!”
表婶愣住,万万没想到,自己这向来乖顺的儿子竟然朝她动了手!
她忽觉世界塌了。歇斯底里起来,一把拽掉麻花辫,疯狂揉,疯狂尖叫,眼底像燃着箭簇,一副要将叶魃吞活剥的样子:“那女人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杨高义,你动手打你老娘!”
杨高义看着这个疯婆娘一样的妈,也不顾一切喊道:“是啊!我就是被她灌迷魂汤了!”
……
杨高义在北京是遭了些罪。节目组片场那几个老板嘉宾都不是省油的灯,说话一针见血,刀刀毙命。杨高义没怎么见过风浪,说话自满夸张,眼神又不够坚定。甚至对自己的人生计划也不够明确,一会儿说想从事行政方面的岗位,一会儿又说对公关感兴趣。像个墙头草飘忽不定,对哪个嘉宾都有点阿谀谄媚的意思。
典型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有个嘉宾老板提醒他:“这套或许在你们小镇上挺有用,但在北京,是个讲本事和理想的地方。本事我们暂时没看到,但是理想呢,你有理想吗?”
杨高义当时还没意识过来,下意识就说:“有啊,科学家,医生,这都是我从小的理想。”
唰――二十盏灯毫不留情地瞬间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