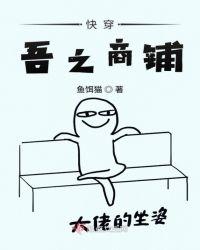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我成了被掉包的罪臣之子 > 201 第二百零一章 给武景同行鞭笞之刑(第1页)
201 第二百零一章 给武景同行鞭笞之刑(第1页)
江州兵船停靠荆北东岸的第一时间,凌湙就得到了消息,派出去的斥候营,将酉二的速绘图给稍了回来。
酉二和酉五从京畿撤回以后,凌湙便将斥候营交予了二人,一个擅听,一个擅隐,这些年搭档着替凌湙跑了许多地方,又有盈芳楼暗中配合,着实探了不少豪门隐秘。
凌湙在边城、陇西府,以及凉州,都办了扫盲班,包括酉一在内的所有亲信,都去修了一轮紧急避险,速绘速记,以及转移藏匿信息时的,简要手语。
其中的手语部分,都是他累积多年的经验,凭着极速狂飙的手势,纵使身陷生死局,也能将想要传递的消息,传到即定之人手中。
当然,这套隐秘手势,只有亲近之人能解其义,另斥候营整队考核,人品素质,以及心性坚毅度,对他的忠诚度,都进行了非常严苛的挑选,后期甚至涉及刑逼、抗药毒的训练,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能通过层层筛选入选斥候营的,其整体位置权重,都不亚于刀营在凌湙心中的分量。
每个斥候营的兵,在凌湙这里都有名字,也因这重视程度,更获得了他们的忠心追随,与刀营一样,成为凌湙绝对可信赖的部下。
凌湙甚至为他们专门拜托了左姬燐,传授一些保命法门,在救援不及时的情况下,好最大限度的保存血线,等待己方施救人员出手,除非身首分离,他保证的是,不放弃,不背离。
来送消息的是斥候二队队长,代号番云,他一面将速绘纸送上,一面沉声秉告,“主子,我们的人从船上传来消息,这批运兵的船只,并非江州出海的那种,是一批被淘汰下来的次等船,故意在临岸时抛锚,拖延登陆时间。”
凌湙将指长的纸卷展开,边看边点头,“猜到了,大帅既然能拉出一批老弱残兵,江州那帮人自然会有样学样,拉几艘破烂船来给朝廷看,都在掩藏实力罢了。”
纸卷徐徐展开,映在上面的船只模样,只有大体结构,上面排列的兵甲倒是按四方位上下站了个严实,没有什么阵列,船头部位甚至摆了酒席,酉二虽然绘的潦草,可该有的全都有,连舞妓的曼妙身姿都绘了个清楚。
江州这领兵的将领,倒不像是来打仗的,出游似的看着甚为逍遥。
番云低头又送上一卷,“这是船只内部构图,是我们的人放了水鸢送过来的。”
凌湙再接手展开,声音带着叹息,“他们离家也五年多了吧?这次任务完成,就收整回队吧!”
刚好可以借着战损,瞒天过海,消弭船内部构造泄密的痕迹。
番云惊喜抬头,眼神震动,“主子,可他们……还没登上海船……”
凌湙垂眼望着他,点头又摇头,“海船那边不着急,现阶段且顾不着那么长远,咱们既已摸清了内河船只的承载量,便不用担心有一日海船入江,这批来的运兵船虽是次品,可基本构造摆在那,有了这份图纸,我就能知道怎么废了它,……起来坐!”
酉一立刻给番云搬了张椅子来,与凌湙对桌而坐,凌湙用镇纸将卷边的两端压住,指着上面绘的各船只内部结构,“……动力源基本靠人工脚踩,底层船壁有铁加固,侧身亦加了铁弦巩固,有箭窗,按了巨弩,船上弓箭手居多,整体船员素质以轻甲为先,少量重刃强甲者压阵,嗯,不错,这五年多没白潜伏,到底是摸到了详实数据。”
番云被夸的挠头,“也是朝廷那边突然提的要求,江州那边很看重五皇子,虽然为出兵之事吵成了一锅粥,可为了五皇子的自由,到底还是同意了太子的提议,这才让我们的人侥幸上了船,虽然是以力夫的身份垫的船底,可正好方便了我们的人绘图,主子交待的动力源机扩构造,都建在船尾,我们的人没费功夫就得到了图,若非他们故意将船只抛锚在离岸五里的水面上,连水鸢都不用,就能送过来,江州兵太安逸了。”
凌湙笑了一声,自八年前打通江州商贸后,他便知道江州船运非常繁茂,再去翻建国史,其中就有高祖因跨不过江,而妥协的条约,他不知道与江州会不会发生龃龉,但对跨江过海的船只却非常感兴趣。
漠河不如东陵江浪大深沉,在凌湙出现在北境前的练兵史上,没有练水兵的先例,整个北境兵将,都是一群旱鸭子,寥寥的会泳者,连漠河都游不过,凌湙亲自站在漠河边,以比赛游泳的方式测过北境人的水性,结果都不甚如意。
北境土生土长的兵将,对水非常恐惧,无事根本不下水,宁可跑死马,也不淌水过。
之后,凌湙便在练兵项目中,加上了泅水的训练,不要求他们能在水中憋气多久,但起码不会一入水就没,为鼓励他们下水,凌湙甚至亲身做了示范,每日领着人往水里去,从身边的酉一等亲信开始集训,训出一批教练后,再去带队,如此年,他手中的兵将,都有了一定的水性,虽然只在漠河中演练过,但换成江,应当也不至于无还手之力。
番云敬佩的望着凌湙,“主子有先见之明,我们的人去到江州,先在码头搬货,踩舢板上下船只,都不带晃的,如此小半年,才通过码头总督办的考察,这才渐渐允许我们往江船上靠,兄弟们虽然没见过大江,可水性都不错,五六年来老老实实靠着江船做活,相熟了不少江州本地船工,大家混居着,连话音后来都改了过来,这才能在此次挑力夫脚工时,混了些人进去,一切都仰赖主子的安排布置。”
潜伏的最根本意志,就是渗透,将自己渗透进当地人群中,与周边人交好,学习周边人的生活习性,讲话口音,做到同质化。
凌湙叫他说的发笑,老大不小的汉子,叫风沙吹的脸显紫膛色,说起肉麻话倒没半点不好意思,遂也就着这气氛开玩笑,“哦?那这些年就没哪个小子在那边成家?江州的姑娘可是全大徵最温柔,脾气最好的,那些小子们就没哄一两个姑娘当媳妇?”
番云骇了一跳,忙从椅子上起身,单膝叩地指天发誓,“那不能,主子,咱们的人都带着任务呢!大家伙知道根在哪里,那江州的姑娘再温柔再美丽,咱也不能动心,主子,我替那帮小子担保,他们绝对没有在那边起花花心肠,连花楼都不去,真的,全光棍着呢!”
凌湙挑眉,示意酉一上前扶人,笑道,“这认真做什么,我也就顺嘴说一说,且若他们真能从江州讨个媳妇回来,那也是他们的本事,人只要用了心,就不怕起歪念,都是大男人,这点把握若都没有,往后能成什么事?再说,把他们叫回来的目地,自然也是他们的年纪到了,与他们一边大的兄弟,在边城、陇西那边,都儿女满地跑了,我啊,是真心希望他们能自己解决人生大事,省得回头还得找我保媒拉奷,你主子我自己也还光棍着呢!”
一翻话说的番云和酉一突突直笑,韩崝和幺鸡正掀了帐帘往里看,就见凌湙难得眉眼俱亮,心情却是近几日最好的样子。
二人立刻踏脚进帐,冲着凌湙下拜,“主子,叫我们?”
酉一替番云搬椅子时,就往帐门处打了个手势,外面守门的亲卫立即去叫了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