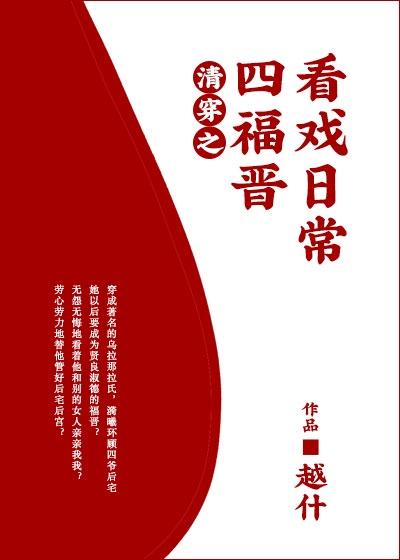墨澜小说>榜下贵婿 > 第91章 我们我们我和你(第1页)
第91章 我们我们我和你(第1页)
京城地界出了这样的事,追杀良民、刺杀朝廷官员,还恰好惊动了禁军统领,封了整条胜民坊抓捕凶徒,这样的惊天消息压根压不下去,京中已然传,现下朝中官员已在纷纷议论。
陆文瀚都觉得自己来晚了——昨夜恰逢宴饮,多饮两杯,歇得太早,底下人不敢打扰,到了今晨才把消息告诉,否则也不至于让玉卿带着一双儿女在别的男人府中住了一宿。
现下,魏卓正坐堂上慢条斯理啜茶陪客,瞧见陆文瀚阴着脸的模样,抬抬手:“陆大人,请喝茶。”
“多谢殿帅,不过陆某今日不是来与殿帅闲话的。昨夜之事,陆某已经听说,承蒙殿帅出手救下玉卿母女,对陆徜施以援手,陆某感激不尽,殿帅请受在下一礼。”陆文瀚说着起身抱拳作揖。
魏卓跟着起身,以掌托住陆文瀚之臂,只道:“陆大人无需多礼,魏某当不起陆大人的谢。”
行伍出身,手劲之力,非陆文瀚可敌。陆文瀚的礼行不下去,也未坚持,直起身道:“也罢,大恩不言谢,改日陆某必当相报。现下还请殿帅让他们出来,陆某想带们归家。”
没错,是来要人的。
听到“归家”一词,魏卓眉梢轻扬,『露』出两分莫测的笑来:“已经着人去请了,陆大人稍安勿躁。”
不论陆文瀚说什么,魏卓都没反驳,颇有些四两拨千斤的味道,倒叫陆文瀚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错觉。
“那就多谢了。”陆文瀚便换了话题,“昨日之事,可知是何人所为?抓到歹人没有?”
“意欲向曾娘和明舒行凶的歹人抓到两名,已经押到我府上,陆大人来之时,本正要前往亲审。”魏卓道。
“随殿帅同往。”陆文瀚道,倒是想瞧瞧,在这汴京城中,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向的妻子儿女下此毒手。
岂料魏卓一口回绝:“此事涉及殿下密令陆徜所查之案,恐怕不便外人『插』手。陆大人若是有,殿下稍后也会前来,你们再议不迟。”
陆文瀚还待再问,却听外面一声通传,陆徜和明舒到了,收起满腹疑虑,转身迎到门口。
陆徜着一袭竹叶青的绸衫,被明舒扶着慢慢踱进屋中。
“殿帅,陆大人。”陆徜依次向陆文瀚和魏卓行礼,一视同仁神『色』,并没对谁格外亲近。
陆文瀚瞧他神『色』苍白、行动迟滞,见明舒颈间那道比昨日颜『色』更深的淤青,脸刷地沉下来。
“你们两的伤势如何了?”疼问道。
“没事,这是小伤。”明舒『摸』『摸』脖子,代陆徜口,“阿兄的伤比较,是箭伤,伤在左肩。”
陆徜闻言望向明舒——这会成“阿兄”了?
明舒以目光回应——不然呢?外人眼中们是兄妹,那他们就是兄妹。她尊敬他,还有意见了?
“……”陆徜默。
“坐下说话吧。”魏卓招呼陆徜坐下,问起的伤势。
“劳殿帅挂怀,晚辈的伤料来应是无碍。”陆徜道。给治疗的大夫是军医,用的『药』也是军中治外伤最好的秘『药』,再加上身体底子不错,昏睡一夜醒来,精神已经恢复大半。
“曾娘呢?怎么没见她……”魏卓点头问道。
“过来前去看过母亲,母亲脚伤未愈,行走不便,想留在房中休养,就不出来见外人了。”陆徜依言坐到椅上回道。
一句“外人”,刺激到了陆文瀚。
“她既不愿出来,那我去见她!”陆文瀚沉声道,语气中已生愠怒。
好好的儿女认不回也就罢了,和变成外人,倒和外人变成一家人不成?瞧曾氏躲在魏卓后宅避不见人,陆徜与明舒也都跟着魏卓的模样,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们才是一家子!
“都说了母亲有伤,需要静养,还望陆大人体谅一二,勿去打扰她。”陆徜半步不让,公事公办的口吻,没给陆文瀚留半分余地。
别看陆文瀚在朝中呼风唤雨,但还是拿这对母子没有一点办法。这二人软硬不吃,夫妻情份父子孝道在他们那里都行不通。与玉卿少年夫妻,和离之时虽吵得天翻地覆,却也恰是情浓时分,这些年纵家中给另娶新『妇』,仕途顺遂,也依旧忘不了她。她之于他,便如间一道白月光,如今既然重逢,自然是想破镜圆,弥补她与儿女这半世凄苦。然而她却不肯再给半点机会,纵他想要认错道歉,哪怕伏低做小重新博她欢,她避而不见之下也是计穷,除非真的耍狠玩阴,将官场那套用到她身上,倒是能够将人抢回后宅,但若他真做了,别说曾玉卿这辈子不会原谅,就是陆徜,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陆徜太像他了,那骨子里透出的骄傲和倔强,几乎与一模一样,甚至比还要犟。当初尚愿意为仕途向家中妥协,但陆徜却丝毫不退。即便番四次向这个儿子示好,甚至表示只要陆徜愿意回陆家,就能入族谱,成为陆家嫡长子,将来不仅有承继权,在官场上亦能得陆家照拂,仕途会比现在顺遂百倍,然而陆徜拒绝了。
陆文瀚听得出来,陆徜的拒绝,绝非以退为进的图谋,而是划清界限的干脆。
“陆徜,不论如何都是你的生父,你就恨我至此,真不愿一家人团聚?明舒,你说说。”在外人家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不好看,但陆文瀚黔驴技穷。
“啊?”被点到名的明舒一下子站直——让她说?她能说什么?前面的误会只是个乌龙,她又不是他们的亲女儿……
“陆大人,你为难她做什么?”陆徜反手按住明舒的手,语气冷了下来,“们又几时与你是一家人了?”
眼见这两人有些争吵的迹象,明舒果断开口:“陆叔,陈年旧爱对错难辩,到如今恩怨俱散,阿娘对你已无爱恨,阿兄自然也不会怨怼于你,只是对来说,慈母抚养二十载,恩重如山,必是要孝敬母亲一辈子的,母亲既无修好之意,阿兄也只会是母亲的儿子。十九年了,阿娘早就放下过去,你也另娶新『妇』,前缘早断,何必执着。”
让她说,那她就直说了。
儿子不帮他,女儿也不帮他,陆文瀚给气得七窍生烟,深呼吸几口,才改变策略开口:“好,此事暂且不提。如今你们遇袭受伤,贼人未擒,危险仍存,陆徜身边人手不够,状元府防备力不足,你们不宜回去,不如先搬到我府上暂住,以策安全。”
这个理由,够正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