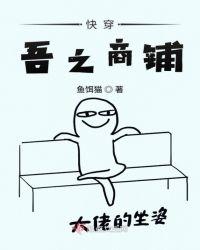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女驸马 > 第 66 章 三告(第1页)
第 66 章 三告(第1页)
“草民盛稀,斗胆状告大理寺卿秋澈秋大人,欺男霸女、强抢民女……导致草民妻子严氏小产,间接致使草民的丈母娘去世……”
“因其乃是大理寺卿,草民实在别无他法,承蒙吴相怜悯,才得以面见天颜……求陛下为草民和妻子连氏做主啊!”
金銮殿上,一布衣男子声泪俱下,不停地磕着头。
李式坐在龙椅上,以吴相为首的太子等一众位高权重的朝臣们,三三两两坐了满殿,除了一旁盘弄着佛珠、闭眼不语的太后,都是面面相觑,各怀心思。
李式沉着脸色,手指在扶手上敲打着,不知在想什么。
不多时,大殿的门打开了。
众目睽睽之下,秋澈被刘不休押了进来——与其说押,不如说是送。
她走在最前面,信步闲庭一般,表情也是一如既往地冷淡镇定。
看了眼跪在地上的男人后,她面露几分适时的诧异,随即不慌不忙地行了一礼:“见过陛下,见过各位大人……臣仓促敢来,不知究竟是发生了何事?”
一众朝臣各怀鬼胎的表情里,吴相倒是显得格外淡定起来:“秋大人此时就莫要装傻了……不如请盛先生辨别一番,这位,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位秋大人啊?”
秋澈冷冷看向身侧匐跪在地的男人。
自称名叫盛稀的男子第一反应是打了个寒颤,接着连连点头:“是他,是他!一日之前,草民在后厨看见的,轻薄我妻子的那狂徒,就是他!”
李式慢悠悠道:“秋爱卿,这位盛先生,指认你一日前的晚上,在他家院子的后厨轻薄他妻子……可有此事啊?”
秋澈掩去眸中冷光,一副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模样,惊诧道:“此话怎讲?臣昨日分明在公主府内,与公主一同入寝才对……院中丫鬟侍卫皆可作证。”
太子阴阳怪气地插话:“公主府中的下人自然是向着秋大人你的,至于四妹嘛,她与你夫妻一体,当然也会为你说话。秋大人的这番证词,可做不得数啊。”
秋澈笑起来:“殿下说的也是,那何不先问问这位盛先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那日侵犯他妻子的,是微臣呢?”
“要知道,臣前几日才刚回京,伤都没好全,放着大好的荣华富贵不要,为什么要大半夜去轻薄人家良家妇女呢?”
李式点点头,很明显对她的说辞很满意。
太子瞧见了,酸水又是一阵阵地往外冒,冷哼一声道:“谁知道你怎么想的。”
吴相则十分意味深长:“秋大人的意思是,盛先生会以这种事,特意来给你泼脏水?”
秋澈也学他,揣着袖子气定神闲道:“臣倒要问问,连证据都没有,这位盛先生是如何确定,那晚轻薄他妻子的人就是我呢?”
盛稀立刻喊冤道:“是臣亲眼所见!绝无半点虚言!”
秋澈步步紧逼,反问:“原来如此……看来盛先生真是爱妻心切,悲痛到连妻子名声都不顾
了,也要将罪魁祸首告上名来……是不是?”()
盛稀下意识点头,又猛地摇头:不不不,草民爱妻,更痛恨小人!此人不除,不知多少良家女子要深受其害≈hellip;≈hellip;当初分明也是秋大人以一己之力,修改了那些让女子们痛苦的恶习,连氏还在草民面前夸赞过秋大人是个好官≈hellip;≈hellip;没想到啊,实在是没想到!
?本作者孟今看提醒您最全的《女驸马》尽在[],域名[(()
一番话说的深明大义,条理清晰——若不是秋澈就是那个被他言之凿凿控诉罪行的人,恐怕都要被他感动到了。
闻言,坐在上首一直没说话的太后,却没忍住笑问:“……既然如此,那为何你妻子受害时,你没有立刻上前阻拦呢?”
盛稀顿了顿,眼中心虚一闪而过,随即又挺起胸膛,坦然道:“草民知晓秋大人有武艺在身,自然不敢与他硬碰硬,此乃草民为夫过失……但这并不能抹去秋大人的罪行!”
太后摇了摇头,而秋澈听着,只觉好笑。
上辈子,她已经不记得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人跪在这里控诉她的“罪行”了,不过说辞都大差不差。
而她因为没有人证,也百口莫辩,在群臣的撺掇之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下了狱。
而今她有人证,虽然不能完全洗清嫌疑,但可要比空口无凭的这位盛先生要有信服力得多。
她倒要看看,这次他们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思及此处,只听那盛稀一咬牙,又接着道:“况且……”
“草民并非毫无证据!草民的妻子连氏,可上公堂作证!”
秋澈饶有趣味的表情,在看到被带上来的女人之后,慢慢凝住了。
她脸上那种一直漫不经心的笑,忽然间一寸寸落了下去,最后重新变成了面无表情。
甚至有几分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