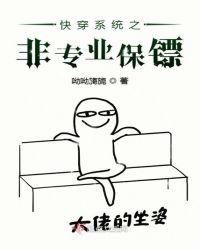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长沙城奇案录 > 第154章(第1页)
第154章(第1页)
祭祀结束,一切如阿檀所料,老管事在送火盆到安远清房中时,故技重施,让阿檀将火盆放到了明式木柜前,随后才颤颤巍巍往外走。
等到夜半时分,外头只剩了风声,安远清才依照计划起身。
他推开木门,外头的寒风刮得他脸颊生疼,心中打鼓,双腿也打颤,但安远清也只能硬着头皮,往正厅的方向走去。
夜色深处,有抹视线一直紧随着安远清,直至见他进了正厅,这人的脸上紧绷的神色,这才放松下来。
果然,都是蠢货,没人能够逃得过他完美的计划。
他就静静站在暗处,静静观察着,等待安远清像他两个叔父一样死亡。
然而,这次,事情却出乎了他的意料,只见正厅大门被打开,刚进去没多久的安远清突然像受到什么惊吓一般,匆匆忙忙跑了出来。
不对,怎么出来了?安远清应该被正厅中的红绸死死缠住脖颈,直至窒息身亡啊!
他悄然跟上去,竟然看到安远清跑过庭院,又回到了三进的主人房,可安远清并未回自己房中,而是走到中央那间屋子前,警惕地环顾四周后,推门走了进去。
怎么进了那里,难不成是发现了什么?
他视线阴暗了几分,隐匿在了黑暗中。
安远清忐忑地在大伯父的房中踱步,不知何时,有个人悄然出现身后,挥舞着一根铁棍过来,可安远清却丝毫未曾察觉。
就在那根铁棍马上要触及到安远清后脑勺时,从暗处蹿出一个敏捷有劲的身影,他轻轻松松,三招两式,铁棍落地,哐当巨响,那人被周钦之牢牢制住,而这时,后知后觉的安远清才顿觉自己险些遇袭,吓得一蹦三米远。
角落中,燃起光亮,阿檀举着一根蜡烛走上前来。
火光跳跃,照亮地上挣扎之人的脸庞,看清的那一瞬间,不仅是阿檀,就连处变不惊的周钦之,也讶然得瞪大双眼。
此人脸颊脖颈,密密麻麻,红斑白屑,层层覆盖,似糜非糜,可怖非常,也难怪那晚谈归箴见过之后直呼怪物。
阿檀头皮发麻,双眉紧蹙走到这人面前:“你是谁?”
这时,冷静下来的安远清也缓慢移步过来,他紧盯着此人面庞,熟悉感很快勾动他尘封的记忆。
安远清嘴皮动动,惊讶得咽了好几下口水,才试探性开口道:“大……伯父……”
门被人从外推开,谈归箴快步踏入,他的视线往下,落到被周钦之制住之人的身上,笃定道:“那晚袭击我的,就是他。”
阿檀蹲下身来,目光与此人平齐,她抿抿唇:“安达山先生?”
意识到被识破,安达山懊丧地闭上了眼。
“我果然没猜错,安达山先生,您并没有去世。”
阿檀往四周看了一圈:“这间屋子被打扫得如此干净,也是因为您就一直生活在这里面。”
许久之后,安达山才睁开眼,他愤然开口:“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阿檀回答:“我不是女佣,他们也不是小工和保镖。”
她走了几步,如实介绍:“这位谈先生,与安远清先生是同窗,他平日好研灵异诡谲之事,因此安远清先生写信告知家族怪事,并邀之同往,破解诅咒谜题,而我们,则是谈先生雇佣过来帮忙的。”
“你们!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其实最开始,我们也一头雾水,直至那晚谈先生偷潜入您房中与您打了照面,我们才知道,安宅之中,有个一直未露面且形容怪异的人存在,白天的时候,又重回您房中查探了一番,发现您房中太过干净,定是经常打扫,有人居住的样子,更让我们起了疑心。”
“还有安达济先生与安达石先生的死亡,离奇地印证了那两句诗文,天降惊雷魂叫冤,鱼水之欢鬼不眠,看起来玄之又玄,可细究死因,才发现非怪力乱神,而是人之所为。”
她有条不紊地说下去:“来安宅之后,每天晚上,老管事都会烧好碳火,给各位安先生的房中送火盆。由于他年老体衰,行动不便,端不动火盆,所以,会叫我这个女佣与他一起。”
“第一天,送火盆安达石房中,老管事从我手中要过了火盆,亲自端到了房中明式木柜前,当晚,安达石从屋顶离奇坠落死亡,第二天,送火盆到安达济房中,老管事以借口,又将火盆放到木柜前,第二晚,安达济死在了水缸中,”阿檀打了个响指,“从这里,我们发现安达济与安达石所住的屋子,靠墙的明式木柜门上都有玄机,这才猜测,而安达济与安达石的死精准对上了那两句诗文,应当与火盆有关,于是就做了个小小的的试验。”
“我们烧了碳火,将火盆端到了安远清先生房里,放置在木柜前,随着温度升高,柜门之上竟然出现红字两行,恰好又印证了第三句诗文,后来,我又拿着这纸片,进入您的房中,找到您的账本,对比字迹之后,才确认您的确没有去世,因为不知道您所藏身何处,所以出此下策,将您引了过来,安达山先生,对此,您还有疑问吗?”
听到这里,安达山才算心服口服,他自嘲地笑了声,停顿,又笑了声,最终昂天癫狂大笑起来。
“我还以为,我们安家终于出了个聪明人,没想到看破的是个外人,可笑,真是太可笑了!”
面对种种,安远清先是难掩震惊,后又因后怕而泪眼模糊:“大伯父,两位叔父是您的亲弟弟,我是您的亲侄儿,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要害死我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