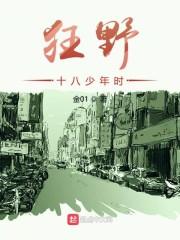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圣母徒弟一朝变成了憨憨 > 第242章(第1页)
第242章(第1页)
钟珝向来不善处理此等棘手的问题,此时面上也尽是烦闷与无可奈何,“一大早便过来了,已经在此处叫喊了近一个时辰了,仍是没有丝毫放弃的意思啊,草!”
宋煊像是没有注意到钟珝的怒意,只是自顾地嘀咕着,“近一个时辰了啊……”
“是啊,一个时辰了,”钟珝也只好强忍着怒意,又重复了一遍。
“天气如此严寒,师兄,你说,我们要不要给他们些棉衣、热水,能暖暖身子也好。”
“……”钟珝霎时呆愣在了原地,许久后方才反应过来,登时怒意更盛,“草!这时候你还能说出这些话!调笑你师兄很好玩是吧?再说,我们哪里还有棉衣?”
这是,倒又变成宋煊的神色恍然变得冷冽不已,肃正至极地言说道:“一晚时间而已,我们便从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仙尊,变成了人人喊打的无耻之徒,师兄,你难道不觉得此事蹊跷得很吗?”
“什么?”钟珝当下一怔,思索片刻后继而言道:“你的意思是……他们受到了挑唆?”
“猜测而已,”宋煊一边轻声言语,一边径直走了出去。
昨晚,他师尊并未再次毒发,但情况尚且仍未见好转,像件供人观赏的瓷器一般安静摆放着,苍白如雪、冰冷至极,毫无生气。
正是因此,这般关头之上,宋煊才不能放任这些事情不管。
……
宋煊与钟珝出现在百姓的视野中时,百姓们叫嚣的声音变小了些,取而代之的则是窃窃私语、小声议论。
“那两人我见过,好像是玄设仙尊的亲传弟子什么的。”
“日日巡夜皆能见到他们二人,现下玄设仙尊许久未曾现过身,说不定便是携着草药逃了,留下两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用作敷衍我们之用,他倒当真能做得出来。”
宋煊环顾四周。
最外的百姓皆是将烦躁与不信任写在了脸上,一些甚至如临大敌一般,手上紧紧握着斧头、钉耙之类的利器,以作不时之需、防身之用。
而驻守的弟子皆是手足无措,似是无奈至极却又只能忍着,不得发作。
宋煊一路向前,没有丝毫惧怕与退缩的意思。
但那张俊美的面庞之上挂着的笑意,却无端令闹事的百姓心生畏惧,并且随着宋煊愈发靠近,适才还不断张扬着叫嚣的百姓却逐渐降低了音量,也停下了撞向弟子的动作。
“诸位,在下知晓那邪毒发作之时,痛楚并非是常人能够忍受的了的,诸位也当真是受苦了。”
“现下如此天寒地冻,诸位切莫要再冻坏了身子。药的方面无需诸位担忧,就算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为诸位寻来,但时限为两天。”
宋煊此话一出,包括钟珝在内的所有人尽皆失了声,皆将意义不明的目光投向这坦然自若又意气风发的少年面上。
无论百姓是否了解,钟珝却是知晓得,现下已经没有药了,无论各门派的贮藏、还是山崖之上。
既然各处都没有,宋煊又将从何处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