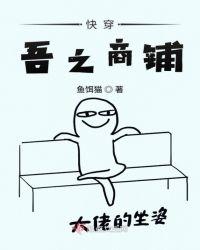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白月光换下了女装 > 115 第 115 章 谁都抵挡不住不(第1页)
115 第 115 章 谁都抵挡不住不(第1页)
实在床笫之地实在太易牵绊住人,以至于方临渊和赵璴在侯府中一直耽搁到了初二的清晨。
初二一早,是吴兴海急匆匆地赶回安平侯府来,说宫中出了大事,请赵璴尽快回宫主持大局。
是鸿佑帝出事了。
他被送回他寝殿之后,层层把守的养心殿之内,就只剩下了他与被放出密室的赵瑾。
按照赵璴的命令,宫中内侍与宫女只在三餐与打扫时入内伺候,其余的时间门,不许进去打扰皇上清修。
可鸿佑帝长在宫里五十年,连自己更衣脱靴都不会,这可怎么“清修”?
更何况,身边还有个满目仇怨地盯着他的亲儿子呢。
据说除夕那日,刚回到寝宫的鸿佑帝才使唤了赵瑾一句,赵瑾便与他激烈争执了起来。
两人没一会儿便吵得厉害,甚至赵瑾还上前用手推搡他。送晚膳的宫女远远在外头,就听见什么“母妃”、什么“父子情分了断”的,并激烈的瓷器碎裂身,匆匆推门入内,这才阻止住他二人,没让他们打起来。
但即便如此,皇上的龙袍也被扯破了衣袖,看起来狼狈极了。
于是,这天夜里,赵瑾自搬去了观景的二层去歇,二人一人占据一层,这才暂且偃旗息鼓。
但是这天清晨,鸿佑帝自己穿靴穿到一半,忽然来了脾气。
据说,他冲上二楼去,和赵瑾激烈争执起来。
可养心殿本就是皇城里最为高大宽阔的宫殿,二层更是离地有数丈之远。守在楼下的侍从还没听见他们二人在吵什么,便眼看着皇上被三皇子失手从二层推下,一路滚下琉璃金瓦,摔落在了殿前的阶上。
皇上不会动了。
宫里急匆匆地寻了太医,可皇上摔到的是后脑,雪地里都淌了一地的鲜血,手足的经脉也因此而失去了操控,连动一下手指头都再不能了。
更别提说话。
赵璴这两日居在侯府里,初二一早便与夫婿大张旗鼓地回宫,半个京城都瞧见了,自然也没人能将皇上重伤的责任推到他身上。
他先将方临渊送回了云台宫,安慰他现在这儿静候其变之后,才径自带人去了鸿佑帝的寝宫。
到养心殿时,里头已经跪满了太医。
赵璴停在龙床旁边,挨个问过了太医们。
半个太医院都在这儿了。他们每个人都摇头,说陛下回天乏术,以后便只能这么活死人似的将养着。
得到了统一的回应,赵璴偏过头去,看向床榻上的鸿佑帝。
他忽然坠楼,周围人只顾着担忧他性命,以至于连被赵瑾扯散的发冠都没人替他整理,此时形容一片狼狈。
更遑论他现下只能眨眼,连嘴都动不了了,下巴脱力,一张嘴只能这么半张着,口涎一路流到了下颌角。
赵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后退半步,嫌弃地皱起眉头。
“擦干净吧。”他说。“你自己不嫌恶心么?”
他居高临下地扫视了鸿佑帝一圈,嘴角很不耐烦地向下扯了扯。
可鸿佑帝哪里还有擦干净的本事呢。
鸿佑帝瞪着他,气得瞳孔都缩紧了,却连斥责他一句都不能。
周遭的太医与侍从也只是将头埋得更低。
陛下眼看着是不中用了,可这位五殿下却是拿了圣旨要承继大统的人。
遑论一个女子登基为帝会面临怎样的腥风血雨,可他们一群奴才,即便五殿下再有多么大不敬,又敢多说什么呢。
没人敢出声,唯一一个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也连自己的口涎都使唤不得,更别提使唤旁人了。
赵璴的目光讥诮地在他脸上停了停,也懒得再跟他废话。
“是说要静养?”他偏头,淡淡问太医道。
太医们连连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