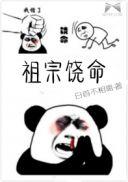墨澜小说>玉人归 > 思华年(第1页)
思华年(第1页)
一夜,风声戚戚,整座瀛客岛皆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恰似夜里陨城云海上的舴艋舟。
三桑跳下云头,拂袖进了结界,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这瀛客岛。
他刚进了院子便嗅到浓浓的酒气。三桑掂量着手里提的酒坛子,瞧她一杯杯饮得痛快,已是微醺,笑骂道,“我还未到,你竟是独酌起来了。”
他还未坐在灵希身旁,便瞥眼瞧见她脖子上的数道指痕,让酒气熏得更红了几分。
三桑拍桌吼道,“怎么弄的?那小子欺负你了?”说着便要去屋里寻衅去。
灵希唤住他,拽住三桑的手腕,“坐下,是我先惹的他。我折磨他,他却不过吓唬我一场……”
三桑闻言仍是紧皱着眉头,“你如今那么能耐,怎么不躲,搞的如此狼狈。”说着便上上下下冲灵希打量起来,瞧瞧还有没有别处的伤。
灵希轻笑,“我这一生,四十万载有余,最后竟是落得孑然一身,可不是狼狈么?”说罢又是满饮一杯。
三桑长叹一声,坐在她身旁,斟了杯酒一饮而尽,辣酒入喉才知她有多愁苦,这酒直呛得他咳嗽,“这酒怎么烈成这样。”
“烈么?”灵希瞧着杯中酒,“我倒觉得不够。”说着便将三桑提来的酒拿来,想要混上一混。
三桑神情微恙,却也未阻她。
只见灵希将坛口的塞子拔出来,凑近细细嗅着,赞道,“好酒,有股梅花香冽之气。”随即斟满。
她忽得长叹一声,抬头望着今日不太规整的月亮,眼角划过一行热泪,掰着手指数道:
“从前我与必兰、龙池、仓毋宁、凌琰还有漆子休,交情不浅,可单是他们这群人,便杀了我两次,两次……”
她冷哼一声,端起酒盅,“从来连声招呼都不打,便叫我为他们牺牲,”她盯着三桑,与他碰杯,“你说,凭什么!”
三桑眉眼微垂,只能轻声劝道,“就算天塌地陷,就算共主疯了灭世,就算连凌煦都黑心负你,永远有我陪你。”
“凌煦?”
灵希冷笑一声,“那日他对我说‘恩怨两销,爱恨双绝’,我与他虽同处一间院子,却已数日不见他了。对他而言,我是不是还不如真的死在东海之畔,好过我们支离破碎……”说着便要举杯一饮而尽。
三桑闻言将手中的两颗三桑玉磨得咯吱作响,猛地伸手将她的酒杯打落,“我的酒淡,不如还是喝你的罢,我陪你一醉方休。”
灵希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必兰仍放心不下我,担心我伤她孩儿,竟连你的主意都打上了。”
三桑有些惊诧,“什么都瞒不过你。”说罢深深埋下了头。
最后关头若不是他动手,灵希明知如此,竟也愿意喝下酒成全他,这让三桑更添亏欠。
她轻笑,“你们以为一杯酒就能了事?也太小看我,太小看我的用心了。”灵希给二人斟满了旧酒,“你是我亲手种下,我怎会和你一般见识。”
三桑顿时来了精神,陪灵希仰头干了满杯酒,算是赔了罪。
“神族如何?”灵希问道。
“你让我观其后效,我一双耳朵里满是凌煦的闲话,拈花惹草,与两女纠缠不清之类,如今他的名声可算是烂得透顶。”
三桑一五一十相告,仔细盯着灵希的神情,却见她毫无波澜,想必是不关心这些闲言碎语。
“对了这是他的朝宗节。”他施决将凌煦的法器幻化出来。
拂袖收了朝宗节,灵希又低声问,“那个姓阿迦的如何?”
“一早便不知所踪,估计回她栀灵山去找她师父去了。不过那凌琰今日一醒便被逐出娥陵殿,下的第一道旨意便是栀灵山主行径不端,幽禁五百年,还要此事绝口,估计经他一治,众多风言风语都能少些。”
三桑交待完毕,不知灵希听了多少,只见她神情迷离,幽幽道,“无有赐婚,也无有交待,这阿迦?怕是被那凌琰白白利用的一颗弃子。”
“我也不信凌煦能做出那等不知检点的事来。你可知他为何会修为微末,为何被锁在蓝田阁里,都是为你受了他姊姊的罚。”
三桑这才得了由头,好好开解她一番,助她断情绝爱,远比不上叫她心想事成。
灵希闻言一蹙蛾眉,“我扔了他的信物,口口声声说过将前情一笔勾销,他竟还肯爱重我么?”
说着她连饮两杯,冷哼一声撇嘴道,“是了,凌家人做的对,他本就该对我避之不及。”
“他受困蓝田阁也并不好过,你别冤枉了他。错在你一向演得不好,若你当真不抱任何希冀,怎么不将真身要走?你若当真要断情,为何还要去蛮荒给他报仇?”三桑一语中的,没留情面。
“回头我将鸳鸯二君的院子捅了,瞧瞧他是不是给我二人系的白绳。”灵希低声笑着,仍是一杯一杯痛饮。
鸳鸯二君乃是夫妻伉俪,掌天地姻缘,红绳定情缘,白绳定孽障。
“你如今和从前不同了,可平心而论,你若只拿凌煦为仇人,不太地道,”三桑凑近她悄声道,“还是你还念着那漆子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