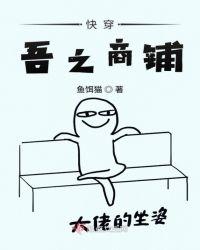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穿成炮灰女配后和反派HE了 > 第117章(第3页)
第117章(第3页)
在最初的慌乱后,承恩公已经定下神了,再次磕头道:“臣因为一己之差点被豫王利用,幸而皇上明察秋毫,才没有酿成大祸。但臣的罪亦是不可饶恕,请皇上降罪。”
旁边的内阁阁老们一个个都是人精,约莫也能猜到怎么回事,对于承恩公能嘴硬到这个地步也是佩服不已。
顾璟紧跟着也跪在了承恩公的身边,也磕了下头,认错道:“父皇,都是儿臣的错,儿臣没有及时纠正外祖父的错误。”
“儿臣今天约了外祖父一叙,本来是想让他查清楚了再弹劾,以免冤枉好人。”
顾璟神情真诚地看着御案后的皇帝,似是恨铁不成钢。
承恩公:“……”
承恩公闭了闭眼,眼底更是一片灰败。
承恩公并没有想把顾璟扯出来,毕竟扯上顾璟也不能减轻自己的罪状,不过是多折进去一个人罢了,但是,顾璟这么着急地与他撇清关系,这种态度让他心更凉了。
他突然就想起了秦准,当初顾璟对秦准也是这样说抛就抛。
说句实话,他知道一些的官员也在私底下议论过二皇子过于冷情,但是没怎么放在心上,觉得是秦准蠢不可及,觉得这种事二皇子怎么也不会弃了他这个外祖父。
直到此刻事情真的临到自己头上,他才感觉到他这个外孙确实凉薄,一旦危及他的利益时,对身边的人毫不留情,根本就没有明主之风。
承恩公觉得心口一阵猛缩,这一刻,悔了。
皇帝眸色幽深,对着袁铭纲道:“袁铭纲,你继续说。”
袁铭纲就继续道:“昨天,锦衣卫昨天暗暗跟着唐逢春到了华鸿茶楼,那时是申初,一炷香后,唐逢春就从茶楼里出来了,之后,一拨人继续跟着唐逢春,另一拨人则将华鸿茶楼包围起来,查抄,拿人,无一个漏网之鱼。”
“跟随唐逢春回二皇子府的几个锦衣卫也一直守在二皇子府外,唐逢春自昨日回府后,就没有再出府,二皇子殿下是今巳初出府,巳时一刻抵达了云宾酒楼。”
“一盏茶后,承恩公也抵达了云宾酒楼,二皇子殿下把账册给了承恩公。”
袁铭纲看也不看顾璟和承恩公,声音沉稳有力。
随着他这字字句句,顾璟和承恩公的额头渗出细密的冷汗,两人的脸上都如墙面般死白,仿佛有一把闸刀架在了他们的头顶上方。
完了,全完了,皇帝什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顾泽之随意地掸了下袍子,就见窗外蛛网上那被蜘蛛撷住的飞虫挣扎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
皇帝面无表情地看着承恩公,再次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承恩公:“……”
承恩公透着青紫色的嘴唇微微颤动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喉头仿佛被什么炙烤似的灼痛不已。
是啊。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还有什么想不明白呢,皇帝一早就让锦衣卫盯着他们了,从他第一次弹劾卫修石之后……不,或者说,远远在那之前!
他要是沉得住气,暂时不动,皇帝也拿他莫可奈何,但凡他们动了,那么皇帝就是以逸待劳。
说穿了,皇帝不是冲着他和顾璟来的,对皇帝来说,他们俩只是用来钓豫王这条大鱼的鱼饵罢了。
承恩公的脖颈乃至后背已经汗湿了一片。
他是臣,也是皇帝的舅父,曾经在先帝在位的最后几年,舅甥之间也是彼此扶持的,一直以来,他自以为对皇帝颇为了解,皇帝从来就是个心软的君主,无论是对儿子,还是对一众老臣。
他一直觉得就算二皇子真的惹恼了皇帝,但皇帝对二皇子总是有一份父子之情的,最多也就是像去岁一样软禁在宫中几个月,最多也就是态度冷淡些……
但是现在……
承恩公不确定了,眸光闪烁。
皇帝不惜拿二皇子当诱饵钓豫王,皇帝就这么眼看着二皇子越陷越深,越行越错……这怕是已经没有多少父子情份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到底是从二皇子娶了唐逢春开始,还是从二皇子纳了秦昕开始,亦或是在那之前,从二皇子与北燕和谈开始……
最近这一年发生的一幕幕如走马灯般在他眼前闪过,承恩公的喉头更干涩了,浑身虚软无力,他已经说不出辩解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