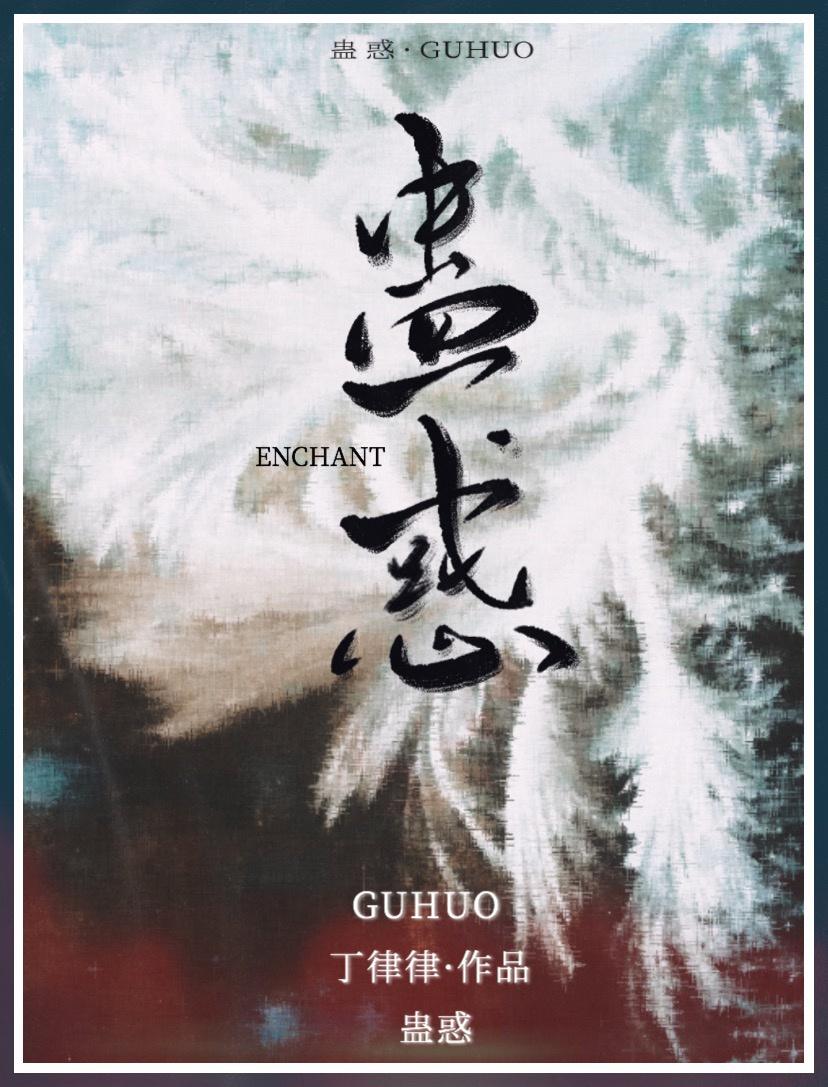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狐媚子 > 尧臣二十四(第2页)
尧臣二十四(第2页)
通悟拜过了文昌君。待他抬头时,文昌君着意观察了他的眼睛。他的瞳仁比凡人略大一些,是蓝黑色的,如海一般。看起来确实特别,却不知这一双神目神在什么地方。
通悟做了文昌君的弟子,开始时候方还规矩,不出几日,便显出本性。这只狐妖性子极为顽劣跳脱。
文昌君殿中有一只灯,灯座之上悬着一轮清辉四撒的圆月,乃是冰雪塑成,是给殿内照明用的。通悟头一次见,便十分喜爱,趁着文昌君不在,把那月灯拔下来蹴鞠。等到释颜发现,那月灯叫他踢在墙上,已经碎成了几片。
文昌君自是大怒,罚通悟禁闭。释颜放心不下,便去查看。
谁知开门一看,内里空空如意——通悟早就跑下界去玩耍了。
当晚文昌君便和释颜发火,道:“兽便是兽……”
通悟从凡间溜回来,便听见师父在殿内大骂自己,急忙“吱呀”一下推开门,跪倒在文昌君面前道歉:“徒儿不是故意惹师父生气,实在是无事可做,成日里待在房里憋闷。想找点事做,谁知却弄坏了师父的东西,反被关了禁闭,连房子也出不来了,实在度日如年,方才跑的。”
文昌君气极反笑道:“你还想干什么?”
通悟的九条尾巴摇摆,抬头道:“我看师父一摸那墙壁,便可去观云台,徒儿还一次没去过呢。下次徒儿跟您一起去如何?”
如何?自然是被拒绝。
但文昌君转念一想,这妖兽精力旺盛,是该给它找些事做,以免它游手好闲,再生事端。但是为防止它闯祸,最好是做些简单的事,便叫他帮着释颜一起抄写文书。
通悟倒是不情不愿地领受了。可是还不到几日,释颜回来一看,见满地散落的都是纸页,案上摊着纸笔,通悟抄到一半,便不见人影。
释颜叹了口气,将地上吹散的纸捡起来,小心地收拢好。往桌前一看,只见那金色墨迹因无人看管,已经渗透了纸张,将写好的字迹沾染成一团。
释颜看到,忙将纸页拎起来左看右看,仍是一大团乱七八糟的墨,心道:坏了坏了,这下上面的名字看不清了,如何是好?
他将纸放在一旁,便去柜子里找他的佛珠,准备施法将其恢复。谁知一开柜门,里面掉出来一个白袍少年,滚睡在了地上,两肩满是烟火气。释颜瞠目结舌:“你又私自下凡了。”
通悟趴在地上,释颜闻见他身上还有浓郁酒气,立马捏住鼻子:“你,你还喝了酒?”
通悟醉得厉害,睫毛颤了一下,闭着眼睛不吭声。
释颜为难地摸了摸自己光滑的发顶,深吸一口气,拈着佛珠念一串经,随后将手放在通悟肩上,叹了口气道:“通悟,通悟,醒醒。一会儿若是师父看出端倪,你就说是我不小心弄洒了墨水,知道了么?”
那脸颊微红的少年叫他晃了两下,猛地翻了个身,摆摆手道:“无妨无妨。”
释颜无奈至极,嘿然一笑:“哪里无妨?”
通悟将手搭在脸上,口齿不清道:“我知道这些人是谁。东阳的宋瑞,王昌明,孙皎;岳阳茂县的刘三;川蜀的于双阳,贾平成……”
此时释颜已经将他放在一旁,拈着佛珠,施法将纸上多余的墨除去。
只不过,此乃神笔,只有文昌君可完全驾驭,以他之仙法,只能恢复七八成。但根据露出来的字迹比划猜测,纸上那些人名,果然如通悟所说,似乎一字不差。释颜迎光看纸,惊喜笑道:“果真如此,你记性不错,抄了一遍便背下了。”
通悟嘟囔道:“我可不是背下的,我是看见的。”
“你如何看见?”释颜只当他说醉话,“你不出这间屋子就能看见?就连师父,都要在那观云台上仔仔细细地看上一日,方能看得准确呢。”
通悟的眼睛微眯,似乎有些迷茫:“怎么看,自然是拿眼睛看啊。”
说罢,打了个酒嗝,不再说话,九条尾巴软倒下来,彻底醉卧于地。
待到文昌君归来,夜晚检查文书,果真发现了墨迹,问了起来。
小和尚释颜本想将此事全部揽在自己头上,可又一想,通悟有此等本事,应加以展现,便将这件事同文昌君说了。
文昌君听完,冷冷一笑。心里想,这妖兽仗着自己聪颖,故弄玄虚,酒后与旁人添油加醋,胡乱吹嘘,心里对他愈加不喜。再加上他早已看不惯通悟轻快浮躁的言行,便想借机敲打敲打他。
于是第二日,他便道:“通悟,你不是一直想去观云台?今日便带你和释颜一起去。”
通悟自是十分兴奋,为不惹师父生气,一路上按捺自己,依葫芦画瓢地学着释颜。
文昌君见他乖顺,也颇为欣慰,决心抛却成见,好好教他。于是文昌君坐在云上,指着下界晃动的人影,仔仔细细地从何为官运,如何判断官运开始讲起。
文昌君做凡人季尧臣时,便做过多年的先生,多年的考官。他授课之时,学生无不全神贯注,洗耳恭听,因此,他最不喜学生溜号。一转过来,见通悟手里捏着衣角,眼神乱飘,神色颇为浮躁,便斥道:“你既然要学看凡人气运,如此态度怎么能学好?”
通悟犹豫一下,道:“师父,不必像您说的那样观气,甚至不必上观云台,我早就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