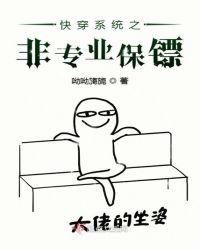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别枝 > 第 68 章 一更(第2页)
第 68 章 一更(第2页)
她搬了把椅子坐在窗边,从纸袋子里,将元禄买来的糖葫芦拿了出来。
即便是冬日,也还是化了一些。
她就这样望着窗外的雪,一点一点舔掉外头裹着的一层糖。
其实,自幼她便不喜冬季,冬季三个月,是她一年中最难熬的。
不仅是屋中炭火不够,须得受冷,更是心里头,总隐隐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怅然。
忽然,“吱呀”一声,闻恕推门进来,正见她对着窗口吹冷风,二话没说便将窗子合上。
“回去之后敢得风寒你试试?”他冷声道。
付茗颂回头,手里那串糖葫芦,每一颗山楂都叫她舔过,糖浆已经全进她嘴里了。
嘴边,还有一抹红糖的色泽。
闻恕瞥了一眼,付茗颂手一缩,不敢让他吃她剩下的,便将糖葫芦放进了纸袋子里。
客栈的条件到底比不上宫里,没有汤婆子,也没有床幔。
梳洗过后,付茗颂抖开被褥,顿了顿问:“皇上,您睡里侧还是外侧?”
“外侧。”
“噢。”
于是,她很自觉的钻进里侧,盖上棉被躺下。
直至身侧的床垫也陷下去,屋中再无其他声音,付茗颂一动不动地仰望着雕梁,静悄悄的夜里,仅能听见她一下、一下,有力的心跳声。
热闹过后的夜晚,总归要清醒一些。
她太明白他今夜对自己的好了,长达十六年的时间,付茗颂从未如此清晰地体会过,何为被人疼着。
她翻了个身,手指轻勾住男人的衣袖,“皇上。”
闻恕闭着眼,并未有回应。
姑娘柔嫩的手指向下,捏住他一根食指晃了晃,“皇上,您睡下了吗?”
男人眉间一蹙,显然未睡下。
但他此举,明摆着不想搭理她。
若是以前,付茗颂还就真不敢再扰他了,但她的胆子,可不就让他给养大的么?
付茗颂轻轻拧了下眉头,半撑起身子打量他,方才还好好的,怎么回来便变了脸色?
她沉思片刻,心中生出一种想法,顿时叫人面红耳赤。
是以,她抿了抿唇,凑近他耳边,试探地,轻轻地,唤了一声:“官人?”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根和脖颈间,再加上
她那一句娇媚动人的“官人”,任柳下惠怕也是按耐不住。
何况,他从来不是柳下惠。
“呜呜——!”
几乎是同时,付茗颂后颈被一只手压下,樱唇“砸”到闻恕嘴角,他细细的吮,拨弄,撬开。
直至她气息不足地推搡他的月凶堂,闻恕方才重重吮了一下,放开她。
他捻了一撮她的长发,在指间缠绕了几圈,“再喊两声。”≈lt;p付茗颂一顿,说实话,对上他这双眼睛,她便喊不出来了。
但他想听吗?若是他高兴,她愿意再唤两声的。比之他做的那些,她这两声“官人”,算的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