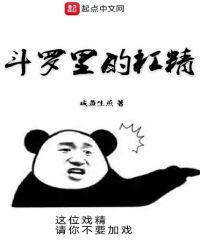墨澜小说>初唐异案 > 371 人言言殊(第2页)
371 人言言殊(第2页)
若非之后两人相谈至久,真人便早已将颜娘携出县狱,寻一安平、寂静处,由颜娘习尽自身平日所修之道术、道法,再由她闯荡于世间。
可偏偏是颜娘,于僵血症、僵血案脱不开分毫关联,而与僵血案所涉之和琢香,却又与东都异骨案中所用灵晶石相干,真人期间重返至东都之时,鳞症已于城中发散开来,鱼怪更是业已现身,接连一串事项,无不与最初那灵晶石之间有千丝万缕之关联。
因此再思及灵晶石,真人便复陷于当初即有过的一番考虑——有关制得灵晶石彼般熟悉之感,究竟从何而来?
带着这番再复于脑中的困惑,真人开始了与圣人接连不断的不时相谈,却迟迟未果。
直至不断自东都传来的地宫、秘所等诸多从未曾听闻过之事项,真人才觉察自身所想,定是曾为人以何法抹消过一段。
自然不是当今圣人,世间又不存任何道法、道术高于自身者,因此无论以相互接触,还是手握取巧之法而论,加之近数日来,渐渐因自身之反复回想,再复现于自身脑中的往事,他才终意识到,武后正是将真人自己脑中一段回想、记忆,篡改、抹消之人。
先皇高宗尚在位时,便央告真人多次,请他制出一两味丹药,以助其回复体能精力,用来再续数年之大统——此举主为将武后废唐夺位之时,尽可能延后
。
而丘真人正是应高宗所求,自创了一味丹药方子,其中所用部分药材,皆为现寻其种而栽种。
然栽种植物,炼制丹药所花时日,终赶不上跃跃欲试将取皇位而代之之武后,亦未曾赶上武后怂恿高宗往泰山封禅,终致高宗自彼时起重病不止。
武后把持朝政后,非她所允,就算是真人也不得轻易入宫参见高宗,唯独有两回,是为真人将高宗所需丹药送入宫中,并执意亲眼目睹高宗将丹药服下——高宗早已与真人说得那般清楚,但对武后防上一手,自然不得使为高宗续命之丹药,离开自己视线。
而就算丘真人将丹药制得,也未尽能将体躯早已全然垮脱之高宗自天命之中救回。
永淳二年,武后自泰山封禅之后,又规劝高宗封禅中岳,而因高宗患病而终止。
而至此一年年末,诏令将以旧年号永淳,改换为新年号弘道,并天下大赦之际,高宗却于贞观殿轰然驾崩。
“想来,正是那时前后,贫道所经之事便未尽回想得完全,似全然颠倒错乱一般,直至眼下才多有复忆起来些许。”
真人再度返于太极宫中,与圣人相谈,说起有关自己一番已然不知为何忘却的往事。
“依老师所言,如此想来,莫非母亲所掌道术,竟已能将入修仙至如老师这般之道人瞒过,甚可操控老师之心绪?”
虽如何都不愿承认,但事实却恰似眼下所言如此,武后不
止私造有地宫、秘所,甚还用术欺瞒过了举国之内至为神通之丘真人。
“只是朕未曾思明,母亲大费周章,最终却未得以异骨、僵血、鳞症达成何样目的,如此究竟是为何故?”
“哲郎如何忘了?早先贫道所言,那晴雨珠与雷云珠二物,只取其一,便得召唤天候,想来两件皆得,或可掌控人心,参晓将来?”
真人从未有如圣人面前此刻所见之茫然,他甚悄然以一手下按脑后穴位玉枕,在自丹田运气,以迅速化精练气,加快对武后当时所言所行之回想。
那时武后得以成异骨、僵血、鳞症三样异症,原欲分别用于万民、臣工、军将体躯之上,但得成之时,已至年岁终末之际,自身亦为各样病痛缠绕折磨,又不愿全然信任身边之人,且此等秘事,实不得由确凿相干但必将因异症受害之人所知。
由此,唯有将此般三症,不分将其施加于其体躯之上之受者,尽数于造筑秘所之工匠身上验试一番,若得行,便直接投于神都、长安城中,任由其自行发展,所谓先乱而后治,武后自觉终仍有几年寿命可续延,或有一日,得于诸事将成之时,终得以屠灭人魈,获长生之法。
与此相干之众人,跨越于数十年,自高宗仍在世时,直到当今圣人再度为国君;由敬晖、张柬之等人仍在世,源乾煜仍于朝堂为朝臣时,至五王尽数殒命,源阳、源协已
然成为医正,人人对此所见,皆有不同,而究其根本,是因武后所行,过于莫测。
但这时随真人之回忆复得,一切或终将得一说法,而此一件事,正如彼时于众人梦中假扮真人之圣人所为一般,当再一回于众人面前,将事情来由说明,才不致言人人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