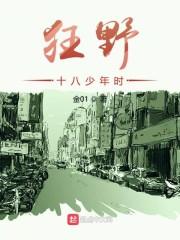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书剑游侠传 > 第五百五十七章 云巅过霜河日落(第1页)
第五百五十七章 云巅过霜河日落(第1页)
薛靖七在帐子里醒来时,日头已经西移。
她睡得很沉,还做了噩梦,惊醒时,神思有些恍惚,手脚后知后觉发凉。
睁开眼,看见的是易剑臣那双黑沉透亮的眼。
心里忽然就稍稍安定了。
他不知何时躺过来的,侧着身,左臂搂着她的腰,目不转睛望着她,眉头轻轻一蹙,柔声问:“你睡得不踏实,一直皱眉,做噩梦了?”
“嗯。”薛靖七垂眼静默了会儿,哑然失笑,轻声回答,“我梦到子清了。她看着我,像是不认识我似的,甚至带有冷漠的杀意,我不知所措,然后就醒了。”
易剑臣没说话,怔怔出神片刻,似是想起什么,搂住她的手臂猛一用力,薛靖七猝不及防,下意识抬手去抵,回过神时,发现自己已整个被圈进他的怀里,额头靠在他宽厚的肩上,冰凉的指尖隔着几层衣衫能触到他温热的胸膛,还有强有力的心跳,一下,又一下。
他左臂依旧紧紧搂住她腰身,右手穿过发间,轻轻抚着她后颈,小心翼翼地用力,将她的全部按进自己怀里。
他们紧密相贴,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和心跳。
薛靖七指尖发烫,动了下,却又无处安放,堪堪仰起半张脸,却看不清他神色,只瞧见下颌微微泛青的胡茬,还有滚了几下却没发出声音的喉结。
“怎么了。”她低低问了句。
她很了解他,他每次突然这样,都是因为什么不太好的事。
“我昨夜也做了噩梦,和你的梦很像……只不过那个人是你。”易剑臣低头,垂下眼眸,去看她,声音有些低涩,语气极为平淡,将什么东西压下去。
她听后却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不动声色地瞧着他,十分认真,仰着的脸干干净净,纯粹得没有半分情绪,没有梦里的杀意,却同梦里一样清冷。
这种平静的坦荡,让他那好不容易压下去的东西,又浮上来。
“傻子,我不会对你有杀意的,此生都不会。”薛靖七忽然笑了下,“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所以你不要害怕。”
他心头一热,又苦笑,轻轻“嗯”了一声,抬手揉了揉她的后颈,正经道:“所以你也不要害怕,梦都是反的,言姑娘和你关系那么好。”
她却没有放松,舒展的眉又蹙到一起,摇头,闷声答:“正是因为关系那么好,我才害怕。我越强大,软肋就越明显,想要对付我的人,若在我这里吃了苦头,恐怕会去找我亲近之人的麻烦。”
薛靖七没把话说下去。
“因为……阿卓姑娘?”他哑声问。
阿卓,是薛靖七第一个至交,也是第一个,因她而死的人。
“你害怕,言姑娘会重蹈覆辙。”
薛靖七没有回答,只是目光不再坦荡,缓缓挪开,望向空处。
她自以为,时至今日,她已想通了很多事,放下了很多事,能潇洒又坦然地面对所有刀山火海,不顾惜一条烂命。
可是她还有牵挂,还有软肋,还有那么几个人……
像一杆长枪,破开看似无坚不摧的铠甲,一枪摧心。
“你看,你和我一样,看似强大,实则脆弱,真是令人难过。”易剑臣看着她眼尾一点一点染红,心里一阵疼,弯了弯唇角扯出一丝笑,低声道。
薛靖七闻言笑了笑,挫败感十足,认真思考了一阵,重又抬眼看他,“所以……剑臣,我想,我们该回江南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易剑臣只是笑,没说话,过了半晌才认真说了句:“从正月十八到现在,十天,阿靖,我们才过了十天平静又快乐的日子。”
薛靖七怔住,呆望着他,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
他又继续笑着说:“这十天,大半时间你还带着伤。时至今日,才基本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