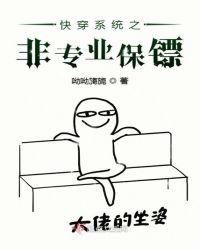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小雪山 > 第一百零一章(第2页)
第一百零一章(第2页)
他第二个星期,果然回来了。
说话相当算话。
他买的记号笔正好一周都洗不掉,思归在学校里一捋袖子就会看到姓盛的讨厌鬼写在自己身上的大字儿,但每次看到都觉得脸红耳热,十分莫名。
周五晚上回家后余思归用沐浴液和热水洗干净胳膊,出去将少爷的袖子一摞,发现他的也还有淡淡的一层。
“你是故意的吧?”龟龟看着自己的胳膊,狐疑地眯起眼睛。
盛淅少爷不太理解,问:“肯定是故意呀,总不能是无心写上去的吧?”
“……”
余思归一下感受到了语言的极限,挫败地说:“我是……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姓盛的混蛋立即展示了个爱莫能助,一摊手,拿了浴巾去洗澡了。
年前他们的相处似乎是处一天少一天,归归格外珍惜他们为数不多的时间——盛淅也是如此。
他们在一起自习,在家一定要磨蹭到最后一刻,在车上就天南海北地聊。
停课后盛淅时间宽裕了不少,大约是周一不用去赶早课的缘故,总是游刃有余的。
思归好奇他的复习情况,盛少爷只笑笑,问:
“你觉得我会有问题吗?”
余思归想了想,忍不住笑了起来。
……
他们谈起其他同学的情况。
一中这届去北京的同学之间有点联系,清北还单独拉了个群,盛淅与前扛把子沈泽关系还成,两人偶尔约着去打个球或怎样——盛淅去隔壁蹭课,还借过他的学生卡。
“你还记得他女朋友吗?”盛淅问。
思归说:“记得……我高三的时候还打听过,那个女孩子最后出国去学艺术了。”
非常坚定的一个女孩子。
余思归仍记得自己高一时曾给她撑伞。十六岁那年,归归见到顾关山的目光甚至会反省自己——对方是认定了方向就不会回头的梦想家。
“你打听她不打听我?”盛淅好笑地问。
思归腹诽再来一次我还是不打听你……盛少爷却移了目光,笑着说:“是,那女生现在在芝加哥,说是寒假也回不来。”
余思归愣了愣,认真地问:“他们还在一起吗?”
“我们也还在一起啊。”
盛少爷笑起来。
思归:“……”
女孩子释然道:“也对。”
“……异国恋好难的。”归归忍不住感慨,“他们两个人也太辛苦了吧。”
同桌开着车,莞尔道:“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思归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温暖,看向旁边不曾离开的盛少爷。
盛淅目视前方开车,温文地问:“所以我这次回家,你一个人没事的吧?”
思归仍觉难过,却已经不再心酸,认真地点了点头: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