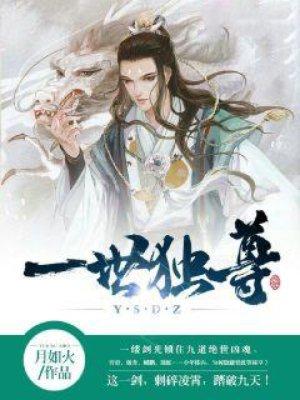墨澜小说>朱门风流 > 第九百章 光风霁月(第2页)
第九百章 光风霁月(第2页)
南城兵马司指挥正六品,顺天府推官从六品,宛平知县正七品。尽管三人的年纪都比张越年长至少一轮,但官阶上的差别却实在是太大,因而这会儿听到那质问,三个人都是面色发白,彼此对视了一眼,那位周指挥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张大人,今天晋王押到京城,不想有几个王府家奴竟是也跟了过来。兴许是听到了谣言,说是皇上要以谋逆罪诛杀晋王,又是杜大人的建言,所以就冲撞了杜夫人。人已经下了顺天府大牢,您不妨问问严推官。”
这皮球一下子就踢到了顺天府,再想到之前宛平知县带着衙役把人押到了顺天府衙,又是说了一大通话,自己原先还觉得人机敏,严推官不禁满肚子邪火,但也只得附和着周指挥的话,一五一十把顺天府衙得报之后将人下狱等等经过婉转道来,最后才低声说道:“这人已经都在牢中,只是还不曾拷问流言来源,下官回去之后,必定报府尹大人彻查……”
严推官讲完,徐知县也不能一味装聋作哑,少不得也将自己知道的那些都禀报了。最后,三个人才忐忑不安地住了口,等着张越开口发话。
“那些人既是王府家奴,顺天府查问此事便有些不合适了,此事上奏之后,自有刑部和大理寺接手。”
原先张越是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但既然此时已经明白了,他便不会把这单纯当成什么冲撞,抑或是报复。家奴之流不过是听人指使,绝望之下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都可能,而背黑锅的人也是现成的,横竖晋王都是万劫不复了,再背一个罪名也无妨。只是,若真的激烈处置晋王,则对藩王是震慑,还是另一种挑动?
而张越这么说了,三个地方官全都是松了一口大气。毕竟,张越没有兴师问罪,反而把这么个大包袱轻轻巧巧从他们身上接了过去。南城兵马司的周指挥忙不迭地表示留下人守卫杜府,而徐知县严推官也忙表示会多派人巡查,张越却说不用,随即把人送到了正堂门口。
“虽则年关已过,但近来京师多事,你们三个衙门都有维持京师治安的职责,便多上点心,否则再出这种事情,休说皇上震怒,便是各处人等,你们也不好安抚。”
张越虽没有点透,但三人哪里不知道,要是别家家眷出这样的大事,绝不是在这儿坐一会冷板凳就能把事情抹平的,因而都是连连点头答应,又提出回头再去拜见杜夫人,却被张越婉言谢绝。
“我家岳父的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些俗套都不用,至于补药大夫之类的也不用费心,杜家什么都不缺,你们只顾好自己的职司就是。”,!
,见张越眉头紧皱,她就招手示意张越坐过来,这才说道,“你岳父今天当值,你回去之后捎带一句话,让他别急着告假,我这儿没事,别耽误了要紧政务。顺天府那几个衙门你也去知会一声,平日该怎么处置,眼下就怎么处置,别因为是我就拼命催逼底下的人。”
听裘氏这么说,张越不禁眉头一挑,看了一眼小五才说道:“岳母,顺天府的一个推官,宛平知县,还有南城兵马指挥使,据说都已经在正堂等了好一会儿了。”
裘氏闻言一愣,随即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又用少有的严厉眼神看着小五:“这是怎么回事,人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娘,您这还受着伤,急着去见他们干什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晾一晾他们有什么打紧……”
话还没说完,小五就心虚地止住了,又低下了头。见她这副模样,裘氏又是真生了气,张越连忙劝慰道:“岳母就先安心养着吧,外头的事情有我去料理。小五,岳母的伤真的只是皮肉伤,没有伤筋动骨?”
小五悄悄别转头擦了擦眼睛,这才低着头说:“只是皮肉伤,我都瞧过了。都是我不好,我跟着娘一起出去,结果娘受了伤,就连背上也青紫了,可我偏一点事都没有……”
裘氏原本还要再告诫小五两句,听她说这话,顿时叹了一口气,一把将她揽在了怀里,这才轻声说:“娘都一把年纪了,就是碰着哪里也不要紧,你小小年纪,有个损伤积下毛病怎么了得?你既然懂医术,给娘治得好好的就行了,说什么傻话……”
见小五依偎在裘氏怀中掉眼泪,又看到裘氏冲自己轻轻点了点头,张越便悄悄退出了屋子,等到了外头,他原本还柔和的脸一下子阴了下来。虽说小五气急败坏迁怒于人不对,但如果那三大衙门真是都没抓着人,那就是他,也非得把那晦气寻到底不可!
杜府的正堂名曰铭心堂,之所以不用那些仁义道德福瑞吉祥之类的字眼,便是杜桢觉得这铭心两个字才是做人的真意,所以,他亲自题上去的这铭心堂三个字高挂在那中央,但凡是踏进这里的人,第一时间便能看到这三个字。尽管那不是什么龙飞凤舞的草书,也不是什么飘逸俊秀的行书,可那三个端方大字放在那里,看到的人不免就想到了冷峻的杜大学士。
此时此刻也是如此,不管是顺天府的严推官,还是宛平县的徐县令,亦或是南城兵马司的周指挥,三个人依着文武分东西而坐,尽管下人们茶水点心照应得还周到,可他们就是有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偏生还不敢起身离去。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始终安安静静的外头突然有一阵响动,紧跟着,那松花色的厚实门帘就被人高高打了起来。可看清楚走进来的那人时,他们无不是吓了一跳。
“张大人!”
张越朝着三人略一颔首便走了过去,却是没有在正中的位子上坐下,而是就站在那里问道:“我也不想听那些拐弯抹角的解释,今天的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南城兵马司指挥正六品,顺天府推官从六品,宛平知县正七品。尽管三人的年纪都比张越年长至少一轮,但官阶上的差别却实在是太大,因而这会儿听到那质问,三个人都是面色发白,彼此对视了一眼,那位周指挥才不得不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张大人,今天晋王押到京城,不想有几个王府家奴竟是也跟了过来。兴许是听到了谣言,说是皇上要以谋逆罪诛杀晋王,又是杜大人的建言,所以就冲撞了杜夫人。人已经下了顺天府大牢,您不妨问问严推官。”
这皮球一下子就踢到了顺天府,再想到之前宛平知县带着衙役把人押到了顺天府衙,又是说了一大通话,自己原先还觉得人机敏,严推官不禁满肚子邪火,但也只得附和着周指挥的话,一五一十把顺天府衙得报之后将人下狱等等经过婉转道来,最后才低声说道:“这人已经都在牢中,只是还不曾拷问流言来源,下官回去之后,必定报府尹大人彻查……”
严推官讲完,徐知县也不能一味装聋作哑,少不得也将自己知道的那些都禀报了。最后,三个人才忐忑不安地住了口,等着张越开口发话。
“那些人既是王府家奴,顺天府查问此事便有些不合适了,此事上奏之后,自有刑部和大理寺接手。”
原先张越是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但既然此时已经明白了,他便不会把这单纯当成什么冲撞,抑或是报复。家奴之流不过是听人指使,绝望之下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都可能,而背黑锅的人也是现成的,横竖晋王都是万劫不复了,再背一个罪名也无妨。只是,若真的激烈处置晋王,则对藩王是震慑,还是另一种挑动?
而张越这么说了,三个地方官全都是松了一口大气。毕竟,张越没有兴师问罪,反而把这么个大包袱轻轻巧巧从他们身上接了过去。南城兵马司的周指挥忙不迭地表示留下人守卫杜府,而徐知县严推官也忙表示会多派人巡查,张越却说不用,随即把人送到了正堂门口。
“虽则年关已过,但近来京师多事,你们三个衙门都有维持京师治安的职责,便多上点心,否则再出这种事情,休说皇上震怒,便是各处人等,你们也不好安抚。”
张越虽没有点透,但三人哪里不知道,要是别家家眷出这样的大事,绝不是在这儿坐一会冷板凳就能把事情抹平的,因而都是连连点头答应,又提出回头再去拜见杜夫人,却被张越婉言谢绝。
“我家岳父的脾气你们都知道,这些俗套都不用,至于补药大夫之类的也不用费心,杜家什么都不缺,你们只顾好自己的职司就是。”,!
,见张越眉头紧皱,她就招手示意张越坐过来,这才说道,“你岳父今天当值,你回去之后捎带一句话,让他别急着告假,我这儿没事,别耽误了要紧政务。顺天府那几个衙门你也去知会一声,平日该怎么处置,眼下就怎么处置,别因为是我就拼命催逼底下的人。”
听裘氏这么说,张越不禁眉头一挑,看了一眼小五才说道:“岳母,顺天府的一个推官,宛平知县,还有南城兵马指挥使,据说都已经在正堂等了好一会儿了。”
裘氏闻言一愣,随即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又用少有的严厉眼神看着小五:“这是怎么回事,人来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娘,您这还受着伤,急着去见他们干什么,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晾一晾他们有什么打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