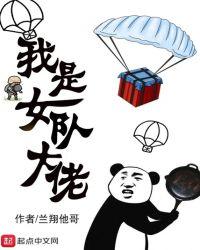墨澜小说>这个炮灰有点东西[快穿] > 64 再消一个 都是好演员(第6页)
64 再消一个 都是好演员(第6页)
打那之后,孙家周围所有人都知道孙母那丧良心的大姐生了个畸形儿丢给孙母自个儿跑路,把孙家给坑惨了。
都觉得那孩子病病歪歪活不长,谁知道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人家愣是顺利活到二十多,谁不说一声“那孩子命硬”!
对这话孙家夫妻的感受最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养那孩子,就是奔着往死了养去的,孩子长成那样,他们看了都瘆得慌。
奶水全给大女儿吃了,老二随便弄点米糊糊,吃多少算多少。一转眼孩子都三岁了,老大送去幼儿园,两口子才猛然意识到老二还挺着一口气活着!
在他们想来,老二脑子都被产钳拽变形了,智力肯定也有问题,上幼儿园是纯纯的浪费,待在家里别惹事,别给他们丢脸就是最大的贡献。
孩子长到三岁,就没出过家门,没穿过完整的衣裳,还是老大要请小朋友上她家过生日,两口子为了不给大女儿丢人,打算带老二出去躲躲,老二才第一回穿上了全乎衣裳。
把孩子在家里关到十岁,一家三口都觉得那是个傻子,饥一顿饱一顿养着,有剩余的饭就让她躲去厨房吃,没有就饿着,反正饿一两顿又不死人。
在外面工作不顺,在学校考试成绩不理想,都回家拿傻子出气。
傻子整天待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多舒服啊!让她做做家务怎么了?衣服要手洗,地板要趴在地上擦,也算是给家里做点贡献。
进进出出嫌弃傻子碍眼,指着她鼻子骂:
“我是倒了八辈子霉才养了你这么个祸害,跟你丧良心的爸妈一个样,倒霉催的!”
谎话说多了,他们自己都信了,下意识觉得老二是大姐家的孩子。
其实在没人注意的地方,这个傻子通过电视机吸取了多少知识没人能知道,家里发生的一切她都默默看在眼里。
直到有一天老大捡了傻子搁在角落的一张五线谱,并在音乐课上鬼使神差当着老师的面儿唱了出来,老师当时就惊为天人,想把老大推荐给他的恩师。
一家人才知道老二并不是全然的傻子。
“我生来就对音乐非常敏感,对周围人和事物的变化感知敏感,在我眼里,一朵花是一段音符,一双筷子是一段音符,路上两个陌生人的对话也可以是一段音符。”
孙明乐看着远处高高的围墙,像是看到了她可悲的一生,声音里无波无澜:
“孙明笑嗓音条件好,但是毫无创作能力,而我,就成了补全她这个短板的工具。甚至为了防止被人发现端倪,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完完整整的坐在一起,商量出了一套只有我们能看明白的密码。
当时我是心甘情愿被她利用的,因为我真的以为我是大姨丢弃的孩子,是孙家给了我一碗饭吃,让我活下来。
直到三年前,我无意中听到他们背着我说事,才知道我竟然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这件事就连孙明笑也早就知道。”
雷鸣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秋东旁边,听的拳头都硬了,牙齿咬的咯吱响。
秋东看了一眼,觉得他这样也挺好的,拍拍他肩膀,给与无声安慰。
孙明乐整理好情绪,掠过当时发现真相后的崩溃,轻描淡写说:
“当时确实精神受了点刺激,孙家人像是甩麻烦一样把我丢到这里,不过我很快就缓过来了,还觉得日子就这样过也挺好的,至少干净。
可孙明笑却不行,她以为没了我,凭借她多年的经验和刻苦学习,也能补全她的这块短板,她这么多年靠我在背后默默付出成就了她创作才女的名声,想必心里也很不自在,于是大多数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了。
但没天赋就是没天赋,勤奋和天赋是两个领域的事,所以她不得不再次低声下气回头找我。他们严格管控我,不让我接触一切电子产品,就连照顾我的护工也被她收买了。
只有孙明笑来的那天,才允许我看她提前准备好的内容,让我从中找灵感进行创作,等到她下再来的时候,我写的东西就会被她带走。
我怕他们恼怒之下断了给医院的费用,又不想让他们好过,索性装作真的精神受了刺激的样子,偶尔写点暗黑风格的东西交差。”
孙明乐笑的很僵硬:
“孙明笑的嗓音,强行和这个风格融合,早晚会出事。”
可不嘛,她明明憋屈的厉害,还要表现出非转型不可,一门心思往这个风格发展的决心,跟脑子有坑似的。
秋东关闭录像功能,保存视频,对仿佛“终于和人分享这个秘密了”的孙明乐说:
“我会找机会把事实公之于众,你别担心和孙家翻脸后医疗费的问题,到时候应该会有人主动找你约曲,你要是喜欢住在这里的话,完全可以靠稿费养活自己。”
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了一个电话号递过去,秋东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联系他,这是我助理,可以帮你处理约曲过程中的一切琐事。”
孙明乐没说话,又对着远处发上呆了,看起来平静极了。
反倒是雷鸣,出了医院范围后,直呼他得缓缓,拉着秋东要去喝几杯,十足感慨:
“住在精神病院的天才,嘿,难怪都说天才总有点与众不同的小毛病呢,这还真是!想想孙明笑那些粉丝知道被他们疯狂吹彩虹屁的作品,是个‘精神病’写出来的,该有多精彩!”
事实上也确实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