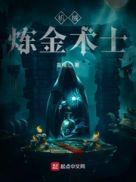墨澜小说>追光 > 66都在想你(第3页)
66都在想你(第3页)
周兮辞想到上一次陈建业来溪城,也被气晕过一次,心里惊了一瞬:“陈叔叔……”
她看着陈临戈,没再继续说下去,靠过去抱了抱他,什么也没说。
高铁抵达沪市已经是晚上,陈临戈在车上给窦彭打了电话,他亲自开车来了高铁站。
见了面,爷俩都很有默契,一个不问一个不提,倒是周兮辞快坐不住了,目光不停在两人之间看来看去。
陈临戈察觉到她的动作,拉过她的手攥在手心里,“怎么了?”
“没事。”周兮辞屈指在他手心里挠了一下。
窦彭从后视镜瞥了眼两人,轻笑了声:“谈恋爱了?”
周兮辞脸一热,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陈临戈却不松手,应得坦然:“嗯,在谈。”
“挺好。”前边是红灯,窦彭缓缓停了下来。
像打开了话茬,陈临戈终于不再沉默:“我爸什么情况?”
“哟,我还以为你能憋一路呢。”窦彭扭头看了眼后边,又很快转回去,言简意赅道:“脑袋里长了个东西,不过问题不大,切了就成。”
周兮辞还来不及感慨他简单粗暴的说话方式,察觉到陈临戈像是抖了一下,沉默着握紧了他的手。
“什么时候的事?”越是这个节点,过往的一切越是清晰,陈临戈想起之前徐慈英生病那阵,陈建业给他打的那个电话。
下一秒,窦彭验证了他的猜测:“一月初查出来的。”
陈临戈有些喘不上来气:“那怎么到现在还没做手术?”
“不用不用,我认识路。”周兮辞把他拽到床边,“陈叔,我走了啊。”
“辛苦了。”她说。
“没事。”陈临戈说:“我就是觉得你在这儿,我安心了很多。”
陈临戈坐在一旁,垂着头沉默了会,拿起搁在长椅的上烟和打火机,也点了根烟。
“反正,反正都过去了。”周兮辞蛮横地将这一页翻了过去,伸手抱住他,“我以后会对你好的。”
他们到医院的时候,陈建业也刚吃过早餐,看到他俩手牵手走进来也没太意外。
“那行。”窦彭确实忙,话都没说上几句,又开车走了。
她抱着一半想知道他的过去,一半想分散他现在注意力的心思,问了句:“你以前都在忙什么啊?”
“习惯了。”陈临戈很轻地笑了笑:“以前很忙,没什么时间想东想西,一闲下来就喜欢坐在那儿发呆,看路过的人,看街边的店铺,看天看树,看脚边的蚂蚁,都挺有意思的。”
“……”
周兮辞笑着一扬胳膊:“走!我请你吃馄饨,吃大碗的!”
“什么?”陈临戈愣了愣。
“我知道啊,但我就是想吃馄饨。”周兮辞买的还是昨晚那家,“你要是想吃别的可以叫前台送,我看了酒店手册,套房的早餐是可以送过来的,反正这两份馄饨我觉得我都能吃完。”
“我们下午吃得晚,还不饿。”周兮辞接过房卡,“窦叔你去忙吧,我们自己待着没事的。”
——怕回不来。
陈建业病情没有陈临戈想的那么严重,窦彭也没说错,确实是切了就没问题,但毕竟是长在脑子里的东西,整个手术过程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以及术后的恢复情况都是未知数。
陈临戈无奈笑了笑,轻轻掐了下她的脸,“好了,打完了。”
斑斓闪烁的灯光,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和远方。
“馄饨?”陈临戈说:“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路边有一家馄饨店。”
周兮辞也是运动员,清楚的知道他们这一行黄金期很短,五年三年,甚至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