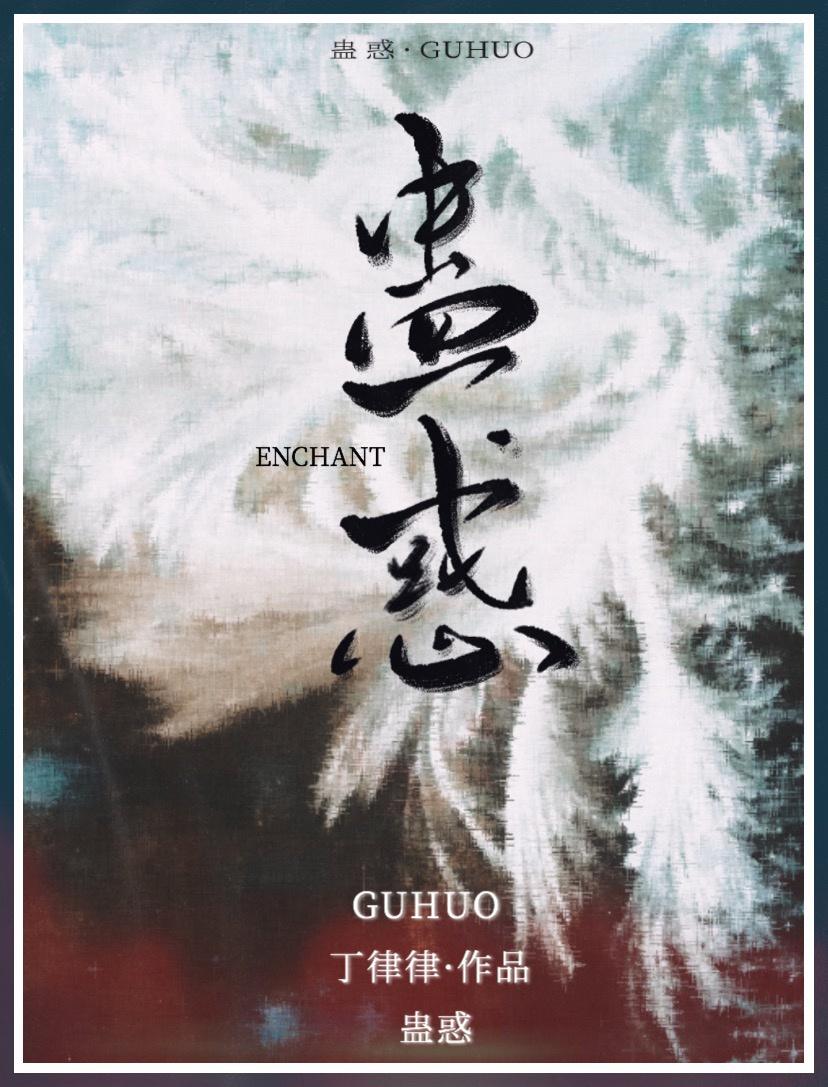墨澜小说>性幻想之重生寡妇x高门判官 > 第四十二章(第2页)
第四十二章(第2页)
“过来瞧瞧我作的画。”王之牧抬起手中的笔打断她的沉思,招呼她到案边。
姜婵依言放下手中的绣棚,袅袅走了过去。
案上画卷长铺,只见千百竿翠竹遮映之间,一带粉垣围城一方小院,数间秀舍环绕一塘水映蓝天。
这莫非是新府的图样?
他既未明言,姜婵也从善如流的未做评论。
他细细瞧了瞧她的神情,又伸手将笔尖调了些胭脂色,扶着她的腕,点点填满那绿树空白的枝丫。
教她写字她便偷懒耍滑,但涉画时却动作仔细、神色一丝不苟。
姜婵太过集中精神,竟连王之牧什么时候稍稍退后,双眼炯炯地观察她将肘枕于画案上,手腕悬起时都未察觉。习与性成,这分明是自然而然使出的提腕技巧,非多年作画功底不能如此习以为常。
王之牧心底几转,撇眸笑道:“蝉娘可觉这画上还缺什么?”
姜婵一双眼全在画中,不觉有诈,顺着他的话就接了下去:“上有翠竹遮映,下有清溪生凉。虽有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之雅,但此处非远离人居之所,便是过于幽静,不如于此处搭起一座秋千,当时父亲……”
话到口边,姜婵心底才猛地一震,面上竭力保持平静,“奴婢的父亲就见过那画上之人家中扎了一家秋千,奴婢不懂这些,只觉得有趣。”
她镇定地将笔搁下,转身却只见他嘴角笑纹未收,目光却是依旧的复杂如深涧。
姜婵本想临渴掘井地说点什么,嘴唇一动,但始终没出口。
王之牧似是早料到她会是这般反应,不急不恼地将探究的目光转回至画卷之上:“如此甚好。”
姜婵脑中如翻江倒海般滚过无数个前后连贯的念头,整个人从发间到足尖都严阵以待,试图以更多的谎言去弥补上一个错漏之处,如临大敌般对准了面前这个背光而立的男人。
王之牧却只待画卷墨干,从容收起,然后长眉斜扬地向她一望:“蝉娘还有何未竟之语要对我说?”
“没……没有。”
王之牧忍不住哈哈大笑,低头吻她,许是方才差点犯了错,她将自己的心结抛到了九霄云外,亡羊补牢地凑过去主动回吻。
这可真是十足的意外之喜了,她这些时日总是躲着他的亲昵,要知她欢喜时就抱着人亲个不停,不喜时便用尽解数躲避不及。
王之牧醉心于唇舌上的温腻触感,吻得情致缠绵,片刻也不舍得松开,仿佛这些时日的不欢而散已被抛之脑后,两人之间又回到了日日交颈时的亲昵。
她贴身抱着他的手时,胸侧不过轻轻碰触了他,就感到他跨间有些异常。她本毫无邪念,无心使媚,却因他的反应弄得微微耳赤。
他的确是忍不得了,夜夜想她,却夜夜须得克制。
他想让她用那藕臂柔柔挂在他颈上,任由他品尝亵玩那敏感的乳儿,大肆出入那会咬人的水穴,在她似痛似乐的呻吟中,将浓稠的精水浇在她身上的每一处,然后让她跪在他身前虔诚地舔净阳具上的残精。
他想用尽一切下流的手段叫她用身体取悦他。
她如今倒像是一头雪润乖巧的小羊主动钻进野兽爪牙之下,这可令他张狂起来,不管不顾地将她按到了榻上,然后一把撩开她的衣裳便埋头而下。
细嫩敏感的乳尖在他齿间扯来捻去,欢愉、疼痛交缠不休、纷至沓来,惹得她忍不住昂颈衔指,苦闷娇啼。
姜婵身怀太多秘密,她如今最大的指望便是等待姜涛的到来,每每依靠他千里之外传来的书信里的美好畅想,她方能枕梦入眠。梦里是她那尚未见过的养蚕缫丝厂、重振余家绣庄的希望、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日子……
可她不知,王之牧如今也有了自己不能说的秘密,那日有孕虽是乌龙,可却在他心中留下了一个影子。
他明知此种幻想是有悖常理的,他的远大抱负和宏伟志向里不应有她,可他每晚的梦里、批阅牒文的间隙却开始不住幻想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如果是个女儿,是不是和她一般玉雪可爱。
这个梦是如此荒诞,可他发现自己如今看到稚儿总是会多留心一些,事实上,皇后之所以赐婚乃是因为一件啼笑皆非的轶事。
那日帝后叙话间,皇后转述起内侍同她所说的有关英国公的的趣事。道是王元卿前几日看到一位年纪相近的同僚喜获麟儿,他竟破天荒地和颜悦色道喜,吓得这位同僚差点晕过去。能被恶名昭着的英国公突然亲近,怕不是自己早已被他盯上了。
能让王元卿做出这样闻所未闻的举动,怕是私下里他想当爹想疯了,同侪都是儿女绕膝,他孤家寡人,圣上也觉得自己是否太过于忽视重臣的终身大事,这才有了皇后赐婚。
想到她和孩子在一起的画面,想到这漫长岁月她永远陪在身侧,越发温柔热情,现在还未产奶,若是当即将她肏至受孕……
王之牧遂不甚文雅地用力吸了一口乳尖,力道大得她痛呼一声,那些不愉悦的疼痛回忆短暂回脑,姜婵立刻挣扎起来。
胡乱推拒中,将他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从冠中扯下几绺,平添了几分与他气质迥异的邪魅。
他丝毫不以为意,爱抚不停。
不查间,她差点踢上他要紧部位,王之牧从唇间放出已被撕扯得红艳的乳尖,旋即更加兴奋,她这番生气勃勃不愿屈服的倔样,反而更激起他的兽性,毕竟哪只猛兽愿意玩弄一只死气沉沉的猎物呢?
津津有趣,他便顺势一手捉了她捣乱的脚踝,破天荒地吻了踝骨一下。这等绝非目无余子的他能做出的事,可他就是做了,还做得如此天经地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