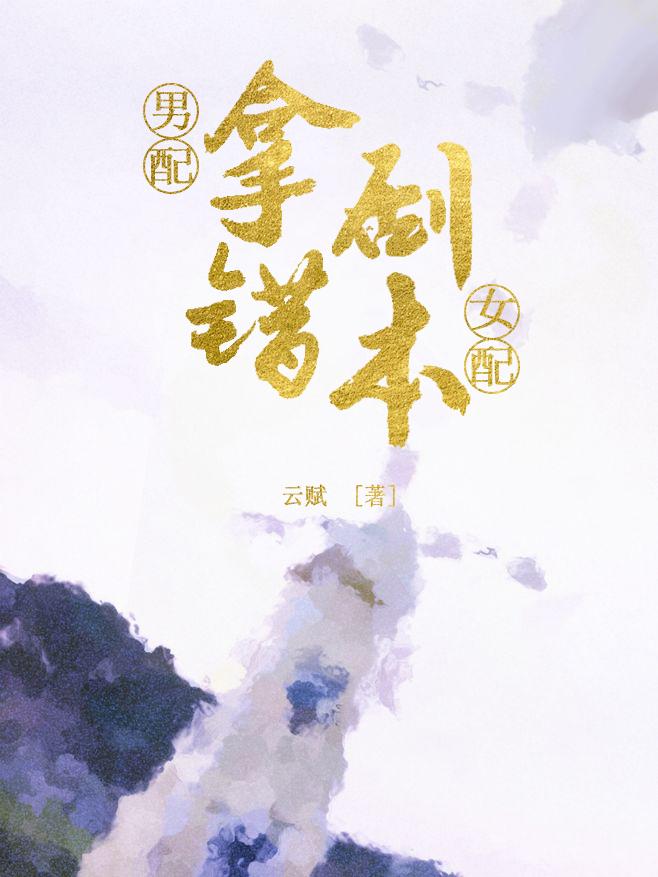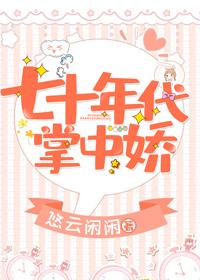墨澜小说>凤鸣朝 > 130140(第19页)
130140(第19页)
“那些披甲带刀的军官见人就杀,扬蹄踏尸,血流成河啊!可怜我县的贺县长,为护我们挡在前面,生生……生生被恶人一刀毙命……”
西北之地民风彪悍,许多绿林草莽听闻,大骂竟然还有这样吃人饭不拉人屎的事!
他们中大多数人,就是因为赋税太重活不下去,对朝廷心怀恶感,才上山落了草。遇到这支规模可观的起义军,众人就如游鱼入水,乳燕投林,揭竿的揭竿,入伍的入伍。
还未到吐谷浑,胤奚又赚得徒卒近万人。
第136章
赫连朵河追在他们屁股后头,眼见逆贼邀买人心,离间百姓,原本濒临绝境的散兵游勇渐有聚团之势,一向作风强硬的关中大行台,也不得不分派文吏安抚民众。
“此皆朝廷叛军妖言惑众,意在谋反。大家生是尉人,可不能信了敌国的奸计!”
然而安抚未靖,尉军后方在这时爆发一件大变——
玄朝的摄政女君发天下檄文,揭露尉国生祭平民的内幕,痛斥暴君无道,扬言发兵北伐。
此文一发,南北震动,直接传到了洛阳尉迟太后的耳朵里。
仍在闷头往西跑的胤奚一行人,此时尚不知情。
高世军眼看着越来越多的流民义士像滚雪球一样聚起来,虽说其中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非常时期,追随者自然多多益善。又仗胤奚怀文善武,分管得当,人皆服他,高世军当初对他那句“不会带兵”的评价,便有失偏颇了。
只是高世军嘴硬不承认。
这日行军路上,高世军以刀尖挑起枯枝上积雪,攥成雪团吞入口中解渴,而后催马与胤奚并驾,粗声瓮气地提醒:“一呼百应是本事,可军中粮食已经见底了。别贪眼前人多,一旦吃不饱,那些本就为混一口饭的非闹起来不可。”
这是他经验之谈。
年前与胞弟的分道扬镳,就是因缺粮内讧。也不知……青州那边情况如何了。
胤奚单手控辔,左手捏了捏酸疲的眉心。
这些日子他每日睡不过两个时辰,白天治军,夜晚警敌,还要想方设法将招纳的三教九流聚沙成塔,令众人勠力同心。
能统领凤翚营的两千人,不过将才,而今两万流兵在他手下井然有序,方见帅才手段。这对胤奚来说不是最困难的,他住在羊肠巷时,便习惯了每夜只睡两三个时辰,只不过是在谢府度过三年睡觉管够、牛乳管饱的安逸生活后,又回到先时的境况罢了。
他心里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他这边深入西境,传信困难,但谢丰年那里一遇袭击,便会立刻回报金陵。
女郎闻讯后,依她智计,不会猜不出他往西去想干什么。
他只担心事起突然,女郎一心扑在军务上,事繁眠少。
若是他在身边,陪吃陪寝,怎么着都能哄劝过来,而今山海阻隔,女郎身边的人谁敢规劝她?
只求她,可怜可怜他,照顾好自己。
别做噩梦。
积雪在难得晴天的西陲碧空下散着莹莹光芒,宛若金絮,胤奚放下手,恢复淡薄神色,应道:“有数。”
高世军打仗在行,打机锋却不行,正想问有什么数,戏小青从侧后方轻策马匹过来。
他向胤奚回报:“统领,打听清楚了。过了前面往北去几里,确有圈地自治的堡坞,只是土人说坞中聚甲蓄兵,自产自足,几不与外界往来,相当排外。”
胤奚神色不变,“南有山越帅,北有堡坞主,皆是一地之雄。咱们这些过路客,该去拜个山头。”
高世军皱了皱眉。
所谓堡坞,是分散在尉朝西北边,三国交界处的一些抱团聚居的宗族,他们的祖辈在当年胡羯入关时为了自保,筑起城堡,坚守不出,从此一代代传承下来。堡出有自种的粟疏,还有鸡园药圃,一切自给自足。
比起山上落草的流匪,堡坞主更像一个藩镇的领主。他们不给朝廷纳税,还无视律法囤铁铸兵,朝廷派兵讨伐,往往攻克不下,铩羽而返。
是以高世军有些估不准,眼下他们后有追兵,胤奚难道还想主动招惹这等不好相与的地头蛇?
他想跟堡坞主借粮,还是攻堡硬抢?
殊不知,胤奚有跟随谢澜安去吴郡收服山越帅的经验,大玄南渡百年,尚且有土断不清、户籍混乱的弊病,他就不信强占中原的尉朝,能将每一寸疆域都治理得服服帖帖。
只要与北朝廷不对付的,都是他拉拢合作的机会。
再坚固的团体,只要有所求,便有得谈。
何况这些堡坞主,多是汉朝遗民。
果不其然,当胤奚仅带精锐几十人,骋至堡城外,举起兵符以汉军名义借粮,有那审势投机的,以字据换粮数十石,有那亲汉恶胡的,亦仗义疏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