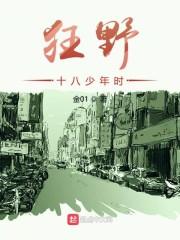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贵妃醉酒 > 第68章 第68章 重重(第1页)
第68章 第68章 重重(第1页)
巳时一刻下朝后,头戴梁冠,身着仙鹤补子图案绯袍的官员,并未与散朝出宫的诸位大臣合流,而是步履生风,向御书房走去。
“臣,给皇上请安。”
“赐座。”
“谢皇上。”低眉顺眼,却难藏锐气的中年人。并未推辞,不卑不亢。
“清远伯府一案,臣已按照皇上的意思,命刑部结案。新任刑部尚书刘基,已将清远伯府的罪状按照皇上所拟条陈示众,燕春楼旧址查封,涉案相关人员皆已下狱,等候发落。”
“清远伯呢?”
“臣,顾及着皇室和中宫的体统,已着清远伯畏罪自尽。”他从绯袍的宽袖中拿出一纸文书,呈于圣前。“这是,臣按照皇上的意思,替清远伯写下的认罪书。”这个黑锅,只能让清远伯府背。
“命刑部、街道司誊抄、张贴,公诸于众吧。”皇上看过,首肯,又将这张薄薄的纸还回他手中。
“是。”他摩挲着自己官袍上的仙鹤图腾暗纹,喜怒不形于色,稳若泰山继续道:“沈宴川听闻慈徽长公主出嫁当日之变故,带领驻扎在津州府的北境军军中的沈家亲信,悖逆生事,已被刘达将军活捉。”
“朕知道。”皇上不假辞色,沉声道:“乱臣贼子…”
“臣请皇上示下。”
“不急,发布十日后依军令斩首沈宴川的消息,让刘达在津洲府再停些天。”
“皇上是想,以此逼出沈庭秋?”他的动作顿了顿,抬眼炯炯有神看向年轻的帝王,“若是,十日后,沈家不反呢?”
“沈宴川行为悖逆,扰乱军心,按军法,当斩!”
“臣明白了。”
“岚琛呢?”
“臣无能,未能找到岚家主和敖登的踪影。”话虽如此,他却是仍然稳稳地在椅子上坐着,神色莫测。“想来…是去北境了。”
“悬赏,边境诸城,一城一城地,在通关要隘,给朕搜。”
“是。”他起身,拱手一礼道:“臣,告退。”
他方才回府,踏入书房院门,抬眼,见清俊温和的年轻人站在不远处投壶,地上已经零零散散倒着十数支箭簇。
“裕王,久等了。”闲庭信步,并未见礼。
“大人是皇兄骨肱,贵人事忙,本王等上一刻又何妨。”裕王回身拿起两支羽箭,分给他一支。观他神色,云淡风轻笑道:“皇兄,焦头烂额了吧?”
“皇上心有沟壑,如今,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人让沈家再苟延残喘几日罢了。”绯红官服尚未换下的长者手持蓝色羽箭,大臂与肩膀平行,将箭矢的端首掷入二矢半远处的双耳龙纹铜壶内。
“岚琛,可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人。”裕王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面无表情的长者,嗤笑一声,自顾自又道:“皇兄原本胜券在握的这局棋,自骆汉骞没能拦住岚琛出京的那一刻开始,变得结局莫测起来。”
“皇上之所以眼下不敢妄动沈家,还是顾及着西郊大营的这块不知去处的兵符。”‘咣啷’第二支箭矢擦壶而过,未中。长者沉吟道:“只要裕王殿下不出手,便是岚琛前往北境搬兵,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皇上,不会输的。”
“华南军十万兵马,萧汇实际上只带回了三万,与东郊大营合流,加上禁军,皇兄于京畿可调动的兵马,林林总总加起来不到十万。津洲府刘达手里有三万,萧汇还藏了过半的华南军不知去向。”狡兔死,走狗烹,萧汇那个老狐狸,是留着兵马自保呢。
裕王漫不经心一瞄,出手,箭矢稳稳当当落入铜壶当中。“西郊大营总共不过五万兵马,本王,从来就不是皇兄的对手。”
“既然如此,王爷今来目的,倒是令老夫不解了。”长者又掷入一箭,呵呵笑道:“在京城这弯急流里,裕王殿下只要不出头,离沈家远远儿的,再看好您手里的兵符,任谁翻了船,也打不湿您的衣角。”
“是啊,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本王真的是沈家和先皇的血脉。而不是…燕春楼的贱子…”二人站在院子里,这处位处京都中心的宅子,正是夕市热闹的时段,却连商贩叫卖的声音都听不到,针落有声。“大人一路暗中扶持本王,十年辛苦,不就是…等着今日吗?”
裕王看着长者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于壶心,动作丝毫不乱。沉声道:“只是本王不懂,大人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要舍近求远,背叛皇兄,转投本王呢?”
“这,与王爷无关。”长者亲力亲为上前,将被掷于壶外的三支箭矢捡起,回到原点重新瞄准投掷。“在下,从未勉强过王爷,不是吗?”
瞄了许久,投出,箭矢在壶边转了一圈落入壶内,不甚顺利。“这兵,出与不出,如何出,全在王爷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