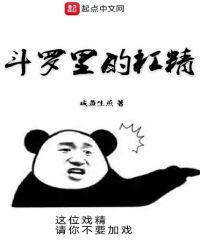墨澜小说>一纸休夫 > 第44章 第44章(第1页)
第44章 第44章(第1页)
夜风送来笙歌声,姬明笙与楼长危互敬了一杯酒,思及彼此乱糟糟的家事,彼此莫可奈何一笑,多思无益,反败坏了良辰美景,不如看看满江繁灯,一城流光。
姬明笙听得岸上打更人敲着锣打着梆子,笑着道:“夜到晚更,外头已经宵禁,将军掌兵马司,总不好以身犯禁,怕是回不去将军府了。”
楼长危轻笑一声:“倒不妨事,我在曲宴坊中有落脚处。”他见姬明笙脸上微露探究,便道,“我少时跟着老师住在深山里,采买方回禹京,来回要两三日,我既不愿回楼家,也为便利,就在坊内置办了一座小院。”后来他身赴边关,屡立战功,姬景元常有屋宅赏赐下来,这处小院便闲置在那,交由几个伤残老兵看管着。
“再者,我老师在这里颇多屋宅。”
“俞圣人?”姬明笙有些讶异。
“老师极喜曲宴的热闹。”楼长危道,世人都以为俞丘声世外高人一个,有惊天地通鬼神之才,超凡脱俗,放诞无羁,视人间万物不过虚妄,只差饮风食露、驾鹤乘云、羽化飞升。
他老师做事随心所欲不假,却也是俗人一个,七老八十看中山下一名渔女的姿容,娶回山中,还生了一个儿子,老人家生怕儿子潦倒,无有金银傍身,未雨绸缪置办了偌大的家业。
俞老仙人道:身无长物,不屑黄白之物,此为酸气横流;身卧金山银山,嫌铜臭扑鼻,此为高洁清雅。腹饥看花,道:此花可食也;仓实赏花,叹:此花将休败,青帝何不怜?我儿得是那知花可食,却惜花时短的怜花人。
因此,俞丘声看似常居深山,不理俗事,实则广布家业,甚至还有几家青楼,为搅名流骚客,他老人家另取名号,亲自动手画了几幅春宫图,听闻已被捧为至圣宝画,风流才子色中饿鬼皆千方百计以图细赏。小师弟将来能挥霍到老死,连带他这个徒弟也跟着沾光,借着老师的商铺矿业,安置了不少从伍行退下的兵卒。
姬明笙神往道:“若有缘,真想拜会俞师啊。”
楼长危笑而不语,姬景元把俞丘声烦得够呛,恨不能远离姬姓人士十里地。
一时,食手做好船宴,鲜落落的鱼虾蟹螺、嬾藕水菜。船菜本是渔家靠水吃水的应付之物,船只离岸后不得回返家中做饭食,便在船上置办一只小小的风炉,挑拣现捕的不好将卖的小鱼小虾,潦草加些盐巴,清煮之后聊以充饥。活鱼活虾,虽少佐料,却也鲜美异常,渐渐便成一方风味,食手来做船宴,再是返璞归真,也不似船家一锅乱煮,需得其鲜美,去其泥腥,味清不夺本味,色浅不失其形。
如意请来的食手,为求在姬明笙跟前得个好脸,拿出毕生的本事,一桌船宴做得鲜香扑鼻,姬明笙将人叫来,赏了金银,食手大喜过望,连连嗑头,红光满面地退了下去。
“与将军相聊甚欢,明知耽误了将军的功夫,还是嫌月移早。”姬明笙双手执杯,正色道。
“交浅言深,亦我所愿。”楼长危同样执杯相敬。
二人一同饮尽杯中酒,相示杯底。
文内侍和如意立在两边伺侯,不约而同对视一眼,哪来的相谈甚欢,他二人听了半天,就没听自家公主与楼将说过多少话,落他们耳里没几句,公主与将军那神色,倒似已过千言万语。
如意拧着眉毛,暗道:公主与将军真是神了,说话都不用张嘴。
文内侍则瞪如意一眼:毛丫头好大的胆,搁心里腹诽公主与将军。
如意平白捱了一眼,一皱鼻子,很不服气地瞪了回去。
姬明笙瞥见他二人在那打眉眼官司,道:“你二人要说话,便好好说话,光在那看鼻子眼的。”
如意眨眨眼,文内侍兜着手,二人齐声道:“回禀公主,奴婢二人无话可说。”
楼长危扫了他们一眼,如意和文内侍一个哆嗦,楼大将军瞧人似能把人瞧个透穿,不安中,就中楼将军道:“怕是在打趣你我。”
如意眼珠差点掉出来,忙道:“没有没有,奴婢没说公主与将军的坏话。”
唉哟,这丫头……这可不就是不打自招了吗?文内侍的老脸,皱得都不成样子,明明生得聪明相,居然是个傻丫头,始料未及啊。
姬明笙与楼长危被她逗笑,笑罢碰饮一杯。
如意气得跺脚,一时忘形,道:“将军竟也是不是好人。”
楼长危一本正经道:“京中也无人说我是好人。”禹京里十个里有九个私下对他大骂出口,剩下一个,是光明正大骂他的。
如意一愣,寻不到反驳的话,气道:“奴婢替公主与将军冰一壶酒去。”
姬明笙笑与楼长危道:“这丫头被我宠坏了,举止粗疏。”
楼长危也笑道:“不失天真烂漫,胆子还大。”
姬明笙挑眉。
楼长危很是坦然道:“我在京中恶名累累,少有小丫头敢跟我放肆。”他亡妻留下的侍婢见他,无一个不是屏气凝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