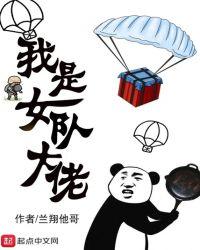墨澜小说>嫁给前夫的皇叔 > 1520(第25页)
1520(第25页)
她自幼生长在落凤城边地,见惯了当地以马为家的民风,对能纵马恣意驰骋风中之事满心向往。若不是她过去年纪太小,阿父定会亲自教她骑术。
好在现在补上这一课也不晚。
萧妄自告奋勇来教导她。
沈盈缺自是一万个不同意。
医者仁心,她虽不是医者,但姑且还是医者的女儿,现在还兼任全天下医者的老大,她当然也有仁心。让一个病得只剩半口气的人从病榻上挣扎起来教她骑马这样的缺德事,别说她干不出来,就算真干出来,也要被身边人谴责到死。
拳拳一片纯善之意,天地可鉴,正常人自然都能理解。
可坏就坏在,萧妄是正常人吗?
显然不是。
从头到尾,他就只有哼哼唧唧阴阳怪气的一句:“你唤我一声‘阿兄’,我教你骑马,有什么不妥吗?不让我教,你还想让谁教?那个还几斤香纂子都要三番四次派人上山磨磨叽叽让再宽限几天的狗东西吗?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沈盈缺:“……”
很想提醒他,那个连香纂子都还不出来的“狗东西”是他的从侄。而且这“狗东西”还不出香纂子,最丢脸的就是皇家,而他也是皇家的人。
然萧妄一甩长袖,却是言之凿凿:“皇族之人更要懂得自立自强,尤其是太子。这么点小事都不能自己承担,还要拖累亲族,当真无用之极。我若是他,早就找块嫩一点的豆腐撞死t?,以证自己心志。”
沈盈缺:“…………”
你高兴就好。
“所以你让槐序托病不来教我,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心志?”沈盈缺板脸又问。
——其实最开始,她的确也想过向萧妄拜师。毕竟论骑射之术,当今世上还没有人能出萧妄之右,哪怕是北边那群生在马背上的胡人也不行。
可考虑到他的身子,还有他的身份,给她当骑术师父,简直比让百草堂去荀家度田还暴殄天物,她也便放弃了,只让槐序来教。
同样是一片拳拳纯善之意,同样是一颗敬重之心。
谁知这货又开始作妖,每天不是找槐序切磋武艺,就是找槐序比试身手,要么就拉着他一起谈天说地,从自己第一次将胡人剖腹挖心是什么感觉,一直说到最近一次凌迟羯兵俘虏用的是什么质地的刀,推荐槐序也试一试,把槐序吓得一整天没敢出门。
教骑术什么的,更是提都没敢再提。
沈盈缺气不过,上门找某人理论。
而某人却是再次一甩长袖,比上回更加理直气壮:“拜师要拜精,不单要学骑术,还要学为人处事的道理。槐序身手固然上佳,可这么点逸闻趣事都能把他吓成这样,足可见其心性一般,不堪为师。为兄帮阿珩筛选了一遍良师益友,也是为阿珩着想,阿珩还有何不满?”
沈盈缺:“………………”
见过不要脸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上辈子能守住城池,统一南北,该不会就是靠这张厚脸皮吧?
但无论怎么扯皮,这骑术师父的重担,最后还是落在了这位“心志独立又心性高尚”的广陵王殿下肩上。
万幸的是,这货虽脾气古怪了些,真教起学来,还是很用心的。
几天学习下来,沈盈缺已经能熟练驾着她的枣红小马,绕着马场周遭的浓荫缓慢散步,无需别人在前头帮她牵缰,可谓进步神速。
这日用完午膳,她便又来马场巩固她的骑术,算作消食。
听见萧妄问她度田之事,便道:“是有那么几个刺头,不过没关系,我能处理好,顺便还能借这机会,把百草堂上下的人也筛上一遍。”
萧妄抬头挑眉,“怎么,百草堂里也有荀家的内鬼?”
沈盈缺挠挠腮,有些不好意思,“也不能说是内鬼,我到底和他们家定过亲,两边之间有来往也不奇怪。我那祖母又是个趋炎附势、任人唯亲的主。这几年,她一直借口说我年纪小,不懂事,帮我打理堂中事务,没少往要紧处塞她的七大姑八大姨,不知道的还以为,现在百草堂已经姓“胡”不姓“月”。索性就借这次度田之事,把他们一勺全烩了,也算因祸得福。”
萧妄嗤笑,“你倒是心宽,就一点不担心他们把你吃了?”
“哎呀,心宽才能活得长久嘛。”沈盈缺甩着马鞭,一副玄之又玄、高深莫测的模样,“看看司马懿,再看看诸葛丞相,活得久,才能笑到最后;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甜。”
萧妄瞪眼,“活得越久越王八,小心一觉醒来,连龟壳都翻不过来。”
沈盈缺也瞪眼,“翻不过来我就不翻了!千年王八万年龟,我顶着那么大一壳儿,压都能压死他们!”
萧妄“噗嗤”笑出声,上下打量她片刻,叹了口气:“当真不需要我帮忙?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你才刚退完亲,可别又把自己折进去了。”
他刻意放缓了语调,声音变得低沉又温柔,像是冬日里的汤泉缓缓流过心涧。
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沈盈缺竟从他微颤的浓睫,和略钝的尾音里,觉出几分落寞和委屈。
可桀骜如萧妄,又怎么会委屈呢?
大约是自己看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