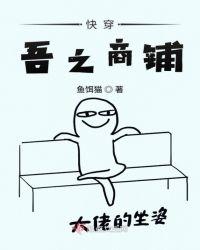墨澜小说>顶流也想做回甜文戏精[娱乐圈]/许我安枕入星辰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许笑笑向司机方向扫了眼,无奈垂头,又从包里取出口罩戴上了。颓丧的情绪,更糟糕了。夜里人少,出租车很快抵达了目的地,许笑笑从车里下来时,一辆救护车正在她面前倒车,她抬头一看,居然是这里。她上次佯装抑郁,是打车过来的,她这回真抑郁了,叫车软件就又将她送了过来。得,这就是缘分。许笑笑虚着步子,来到了位于三楼的精神医学科。除了一位保洁工,候诊区阒无一人,她径直走向那间熟悉的诊室,手一抬,诊室的门竟然自动开了。正要下班的温淮安左手还搭在门把上,看到眼前的人,脚下一顿,眼底划过了一瞬诧异。半晌,许笑笑一把扯下了口罩,“你给我开药吧,治抑郁的那种。”门里的人眸光一偏,看到了对方胸口处的一片酒渍。空气有短暂的凝结。整个病区甚至安静得有些诡异。一位值班护士从门外路过,放慢脚步的同时,目光在两人身上停留了许久。“进来说吧。”温淮安侧过身,示意对方进来。许笑笑沉默良久,似一株摇摇欲坠的雏菊向前迈了一小步。她缓缓摘下墨镜,仿佛摘下的是一顶镣铐,而后,看向了那双清亮的瞳仁。她眨了下眼,又眨了下眼,两颗泪珠便悄无声息的落了下来。这里喧哗褪去,空气中却还残有消毒水的气味。她不想哭的,心说是这气味熏湿了眼。温淮安的目光柔和起来,“我下班了,要不,你先跟我走吧。”。……许笑笑坐到车上时,眼泪还像断了线的珠子。她上一次哭,已经是很久前的事了,还是因为拍戏,剧情需要她哭。但要问她动真感情的黯然泪下,是何时?在何地?为何事?她就记不清了。开开心心的不好吗,流眼泪伤神又伤身,最划不来。这是她好多年前说过的话。第一次挨过父亲的打之后,她就想清楚了,许家的那些破烂事,到她这儿不能翻天不准覆地,许家的那些人也别想在她这儿撒野逞凶。总而言之,那一家人根本不值得她动感情。流眼泪,就更不可能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被鄙弃被讨厌被排挤的事,不仅被人摆到了台面上,她还挨了打。她不甘。车还停在车库里,温淮安看着仍在啜泣的人,平静的问:“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了吗?”他的声音平和,冷静,既没有宽慰的话,也没有安抚的词。但他的眼里,出现了一丝不忍的情绪。“其实……你之前都说对了……我这个人,”许笑笑抹了把泪,“我这个人缺乏亲密关系。”“我觉得……我活到这么大,好像做什么事都在被人否认……”“以前不觉得,现在就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许笑笑想遏制住抽泣,但泪珠不听使唤,一颗又一颗的往外冒,“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网上被人骂,家里被人骂,刚刚——”刚刚,还被亲生父亲当众扇了巴掌。她一想到这儿,就再次哽咽起来。她不明白,她的身上也流着许旺东的血,为何自己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她年幼时想不通。如今还是想不通。许笑笑用手捂住眼,眼泪太多,她就用口罩擦起来。好像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屈,在她体内冲撞、翻腾,以至于最后都幻化成眼泪喷涌出来。温淮安从中央扶手抽了张纸巾递过去,“那你觉得——你是真的有问题吗?”许笑笑接过纸巾,沉默中,竟觉得这是个天大的难题。“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既然不知道,就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一双通红的眼看过去,定格在温淮安的脸上。许笑笑心头一热,眼泪唰的一下又涌了出来。从来没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她看着他,心脏似乎有片刻的暂停。她一直以为,成年人的世界是无需慰藉的。有的,只是竞争,无休无止、没完没了的竞争。她妈妈说,她要与那四姐妹争。五哥说,她要学会与同行争。猛仔说,她要和一同走红毯的人争。甘菊说,我们要和更年轻的人争。又或者,有的,只是诅咒与被诅咒的关系。黑粉说:糊穿地心的人,怎么还不退圈?黑粉又说:看到她的脸就恶心,整容也挽救不了那张野种脸。黑粉还说:小三的种,以后肯定也是当小三!汶川地震,就应该震死她和她妈!许笑笑以前和猛仔开玩笑,说黑粉的那些话又不是当着她的面说,隔着屏幕的键盘侠,哪有那么大的杀伤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