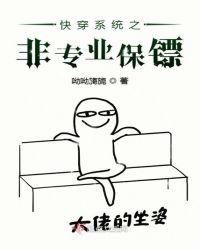墨澜小说>武状元养夫记 > 第114章(第2页)
第114章(第2页)
事到如此,钟离淮不再勉强,只道人各有志。
……
穿过茫茫荒漠,才见冰山与草原割裂的奇境,一面洁白若栀,一面绿草如茵。
“公子,马上到崖关了。”
崖关乃是大戎与凉州的交界地。
月琅轻微点头,干裂的嘴唇微张,发出嘶哑的声音:“万事小心。”这凉州守备诛了知府,彻底反叛,雄据在了凉州。
众人点头,一路走来,只听这大戎又来犯崖关,两军正在交战。
月琅看了眼身后黄土,又瞧瞧前头的雪山草地,犹豫不绝。
旁边的人似乎看出他的犹豫,道:“公子可是在想路上的所见所闻?”
“你猜的不错,与我所想的不同,这凉州并没有乱,百姓安居乐业,一切井井有条,可……那大戎人真能因这些财物拔刀向齐吗?”
“公子多虑了。”
“不,反而是想少了,我以为凉州混乱,是反贼,所以不可交,但事实相反,我认为大戎贪,能以利诱之,可……我并未与他们打过交道,只是臆测罢了。”月琅摸了把脸,多日的风吹雨淋让这张脸粗糙不少,自嘲道:“果然啊,人不能自以为是。”
栖皇孙
“公子惊才绝艳,不心妄自菲薄。”一时也估摸不到公子的心思,只觉心情大抵非常不好,下意识安慰。
月琅叹口气,鸦青的睫羽垂下又掀开,定定瞧向雪山与草地,这情景就好似春天与冬日猝不及防相遇,缺少过渡,显得生硬,却又隐隐觉得,本该如此。低头,自嘲一笑,真是……想什么呢,自个儿都觉着莫名其妙。
“瞧!前面有水,这可是雪山之水,平日可是见不到的,去打些,再洗洗被黄沙弄脏的脸,才好赶赴下一程。”月琅素白的手覆着薄薄的沙土,甲缝间也藏着沙,指甲伸的笔直,定定指向雪山底下的小溪。
这溪水冰泠泠的,刚下手,觉得冷,一瞬,便是刺骨的寒意。月琅忍着寒意,将双手洗得干干净净。
“咩咩咩~”有几只雪白的羊从绿草地冒出圆溜溜的脑袋,吃一口气,抬头叫几句,伴随着几声鞭子掠空的声音,成群的羊急匆匆奔过来,停在溪旁,舔砥着甘冽的溪水。
羊群后的放羊人也从那边绿草地后冒出了头,三个人,佝偻的是父亲,强壮高大的是两个儿子,相像地很,一样的毡帽,一样的羊皮袍,还有同样的大胡子和红脸蛋。
虽然他们只是放羊人,但他们仍不敢掉以轻心,不动声色地往马车旁靠靠,呈防卫之势。
那三人见他们也是惊奇,一看穿着,笃定他们不是凉州人,父亲道:“你们这是往哪里去?不过,去哪儿也不要往前走,前头在打杖哩!打杖知道伐?戎人凶地很,一刀就是一个脑瓜。”
月琅行了个简单的礼,虽形容狼狈,但进退有度,看得出,教养极好,面不改色地撒谎:“老伯,我乃守备旧识,此番是去帮他。”
这放羊的老父亲还没见过这样儒雅的人,一瞧就饱续诗书,不由添几分好感,一听是守备的旧识,越发觉得亲切,滔滔不绝:“这好说哩!梁守备,可厉害了……”